經濟觀察報 關注
2025-08-01 15:19

![]()

2020年荷蘭王室曾在海牙王宮花園拍攝全家福。阿根廷八卦新聞雜志《Caras》選用這組照片作為封面,主打大公主阿瑪利亞,配文是“阿瑪利亞公主自豪地展示了自己的大碼身材”,還著重突出“大碼”一詞。
此舉招來無數批評,人們認為雜志如此大張旗鼓評論一個當時才16歲的孩子的身材,完全就是羞辱。在現實中,這樣的惡意無處不在,有時會以勵志的方式呈現,很多人將之稱為“身材管理”。
身材焦慮和容貌焦慮在全球各地和各個階層都或多或少存在。它的本質是極端的審美定義,比如中國社會對“白幼瘦”的吹捧,西方社會對健康膚色的刻意贊美,部分群體對體脂率的極致追求。個體對自己有所要求當然是個人自由,但一些社會和部分群體將之視為衡量他人的標準,就會造成扭曲。
早在1991年,英國學者娜奧米·沃爾夫就在《美貌的神話:美的幻象如何束縛女性》一書中寫道:
不少女性盡其記憶之所及,寫信或親口向我吐露她們經歷過的惱人的個人戰爭。通過這些戰爭,她們從那種被確認為美貌神話的東西中脫身,找到自我。將這些女性聯合在一起的并非她們的外表:無論是年輕的還是年老的女性,都向我訴說了對衰老的恐懼;無論是苗條的還是肥胖的女性,都提到了因努力去滿足纖瘦理念的要求而遭受的折磨;無論是黑色人種、棕色人種還是白色人種的女性——這些人看起來就像時尚模特——都承認從能有意識思考的那一刻起,她們就知道理想的女人是個高挑、纖瘦、白皙的金發女郎,她的臉龐上沒有一絲毛孔、不對稱或瑕疵,她是一個完全‘完美’的女性,是她們無論如何都認為自己不會成為的那種女性。
在娜奧米·沃爾夫看來,“女性永遠不夠美”,繼而將美貌視為“義務”,把鏡子變成刑具,將“變美”視為終身工作,是消費時代的一整套謊言。容貌焦慮的痛苦,其實只是某些人的生意,允許自己“不完美”,實際上是針對顏值霸權的反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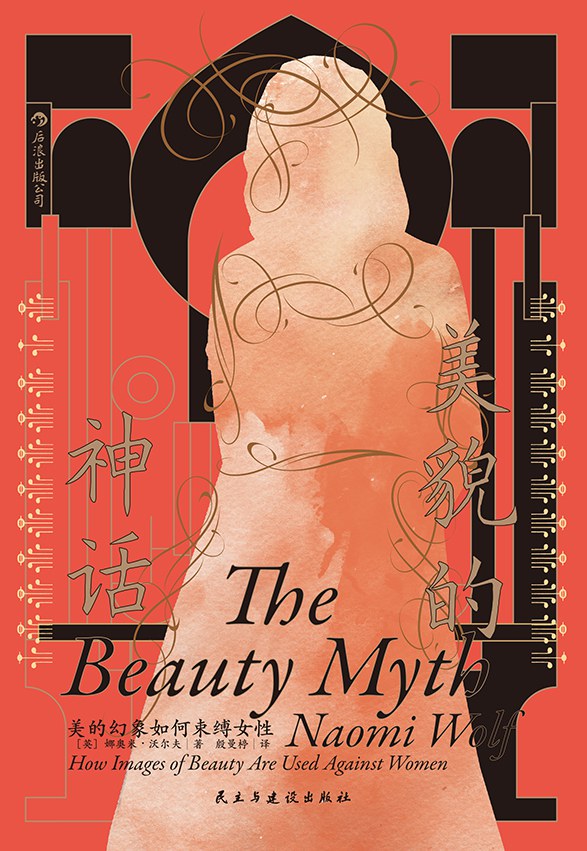
《美貌的神話:美的幻象如何束縛女性》
[英] 娜奧米·沃爾夫
殷曼楟| 譯
后浪| 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2025年5月
30多年后的今天,《美貌的神話》已是當之無愧的“覺醒之書”,被《衛報》列入“改變世界的10本女性主義經典”。它被牛津和哈佛等高校列入性別研究指定教材,因為它引發的社會討論,促使多家時尚雜志取消過度修圖,也側面推動歐美立法限制整容廣告對未成年人的投放,并為反外貌歧視運動提供理論基礎。
但容貌焦慮仍然桎梏著無數女性,社交平臺上的美顏濾鏡、醫美廣告和算法推送,強化著對“完美”的追求,即使商家對這種完美不可能實現的事實心知肚明。除了消費主義的侵蝕之外,社會的“凝視”也構筑著這道焦慮之墻。社會對女性容貌和身體的規訓,依然顯得根深蒂固。
束縛女性的枷鎖中,對美貌的苛求最為頑固和隱秘
如果基于文明社會的正常價值觀,減肥、健身、追求容貌美都是個人自由,但如果將審美標準單一化,將“身材管理”極端化,就會造成自身的焦慮或對他人的羞辱。
也就是說,批評這種現象,并不是批評“美”,也不是批評“追求美”的某個具體行為,而是批評單一和極端化的傾向。正如娜奧米·沃爾夫所言:“評論者經常或是蓄意或是漫不經心地(但每次都是錯誤地)認為我宣稱女性不應該剃腿毛或涂唇膏。上述理解實際上是一種誤解,因為我支持的是女性具有選擇她自己想要的外貌的權利,具有選擇她自己想要成為的人的權利,而不是去服從市場力量以及某個數十億美元的廣告產業所規定的標準。”
在沃爾夫看來,化妝品廣告等消費場域對“美”的定義,營造了關于美貌的理想形象,進而讓女性相信個體應努力符合這種形象,但這實則是規訓女性的社會暴力,不但制造焦慮,也抹殺了過往女性解放曾經給女性帶來的自由。
即使到了今天,女性的權利和境況已經大大改善,但狹隘的“美”仍然框死了太多女性的認知乃至人生。女性看似擁有了選擇的空間,但不管“是否化妝,體重是增加還是減少,是動了手術還是沒動手術,是盛裝打扮還是衣著樸素,以及是讓我們的服裝、臉孔和身體都成了藝術品,還是全然忽略裝飾”,真正的問題仍然是“缺少選擇”。
但若認為這一切都是消費主義的陷阱,顯然是沒有對準靶心。《美貌的神話》試圖推導出這樣一條路徑:當女性從家庭生活中走出,爭取到工作、選舉等越來越多的權力時,“美麗”作為反對女性進步的武器,意圖再次控制女性。
父權社會與資本社會合力為女性建立了美貌的標準和規則,中國社會推崇的“白幼瘦”就是典型例子。為這套美貌標準配套的,還有各種衣著穿搭、化妝技巧和修圖技巧等。女性獲得美貌,就會獲得所謂的“資本”,以美貌換取有限的機會、社會關系、虛妄的安全感和自以為的認同感。這些“收獲”會讓不少女性誤以為自己得到了“獨立”,實際上仍然處于父權社會凝視的斗獸場,處于殘酷的雌競中。
《美貌的神話》以“工作”“文化”“宗教”“性”“饑餓”“暴力”這6個領域呈現女性在美麗陷阱中的命運。
在職場和社交領域,女性的美貌成為被男性凝視與篩選的標準;在文化領域,廣告和大眾媒體的刻意渲染和滾動轟炸,使得美貌成為女性的“自我審查標準”;在宗教領域,美貌和“身材管理”被視為“自律”,甚至成為許多女性自我價值認同的來源;在性領域,美貌成為被物化和被羞辱的誘因;至于饑餓,那些瘦身女性在所謂的自律和羞恥感中一次次自我規訓,以“抵御”饑餓感;暴力則無處不在,從現實到網絡,從嘲笑、惡意評價到“物理攻擊”,女性時常會因為“不夠美”或“太美”而遭遇各種侵害。
在沃爾夫看來,在此之前,“母親神話化”“家庭神話化”“貞潔神話化”“被動與依賴神話化”早已先后登場,他們通過強調母親的“無私奉獻”、女性應該對家庭“無條件付出”、女性應該為自己的“貞潔”負責、女性依賴男性所以理應順從,來實現控制女性的目的。當這幾個神話一個個被揭穿,“美貌的神話”便登場了。
早在工業時代初期,“美貌的神話”其實就已經啟動。從影印技術到攝影技術,再到其后的影像技術和如今的美顏軟件,技術的變革一再加強著“理想美女”的形象固化。
走出家庭、步入職場的女性們,往往還沒來得及發揮自己的才智,便又陷入控制飲食和提升顏值的怪圈。數據顯示,時尚模特體重比正常女性要輕23%,追逐模特身材必然導致與吃相關的疾病呈指數增加,當食物和體重破壞了女性心理平衡后,大量神經衰弱癥患者出現。正如書中所說,節食是“女性史上最有效的政治鎮靜劑”。
在女性被封閉于家中的時代,女性的美僅僅源于其行為舉止,社會大眾也并沒有對女性美有過分狹隘的定義和要求,但在“美貌神話”的時代,女性面對的是對外貌的苛求。那些“丑女”“老女人”之類的定義和惡意,是男權指揮棒下的定向傷害,最悲哀的是,許多女性也不自覺地參與其中。物質上的日益豐足并沒有讓這些女性走向更加獨立的一面,反而心靈更加脆弱,很容易遭遇打擊。沃爾夫認為,這本質上是一種被營造的恐懼,利用了女性的羞恥心。
當“美貌指數”成為社會的貨幣體系
沃爾夫認為,現代西方經濟非常依賴于女性的持續消費,而這種持續消費所依托的就是“美貌神話”營造的氛圍。她繼而認為,社會經濟的本質是依賴奴性的需要,營造奴性的美好想象,進而使得奴性機制順利維持,這一切的基礎就是女性為了滿足男性的構想,迎合狹隘的“美”并為之付出一切,放棄自己最不應該放棄的那些東西——比如獨立性和尊嚴。
在這個機制之下,女性的“美貌指數”成為社會的貨幣體系。女性投入勞動力市場,原本是女性權利的關鍵一步,使眾多女性獲取經濟上的獨立,繼而爭取更多權利。但“美貌神話”引入之后,女性在職場中的地位和財富往往或多或少由美貌決定。模特、娛樂圈這樣的行當自不必說,顏值和身材在大多數時候都是第一競爭力,這些舞臺上的女性在薪酬體系里會占據相當高的位置。
即使在政壇和公司,美貌也非常重要。1960年代,大批接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女性步入西方職場,這被視為改變女性地位的重大機遇,但與此同時,空姐、行政秘書等職業都被賦予性感意味,成為被凝視的對象,甚至成為色情片重要的題材對象,這也使得眾多年輕女性被鉗制,逐漸接受這些工作崗位的“性感”束縛。
喜歡抬杠的人會舉出不少反例,認為總有一些無視美貌神話的優秀女性脫穎而出,但她們付出的努力往往要比同等智力、學歷和能力條件的男性或美女大上很多倍。而且得到上位機會的優秀女性,也往往要妥協于社會的美貌需求,引入美貌女下屬,以便于工作中的“更好溝通”。女性為了職場競爭,將大量收入投放于養顏等方面,早已是常態。
歷史上也是如此。沃爾夫寫道:“一個世紀前,正常的女性活動,特別是爭取權力的那些被認為是丑陋和病態的,一個女性如果閱讀太多,她的子宮就會萎縮。如果她堅持閱讀,她的生殖系統就會崩塌”,維多利亞時代會提議人們多去思考高等教育對女性生殖器官造成的損害,公然宣稱“延長工作時間會導致女性骨盆畸形”“女性接受教育將會讓她們失去生育能力”“一個女性表現出對科學的興趣,她的性將會出現問題”。
這些宣揚一方面是男性對女性“品質”的要求,一方面也是資本的驅動。維多利亞時代的醫學體系,將女性的正常生理現象或心理需求都視為疾病,繼而讓她們求醫問藥。如今也一樣,外科手術時代對“美”的定義,催生了減肥藥、整容手術等暴利行業。在美國年增長率達到10%(其他國家甚至更高)的整容行業,實際上提高了女性的痛苦下限。而且這個痛苦并不僅僅是忍受手術本身帶來的生理痛苦,還有手術之前的長期自我否定帶來的心理痛苦。沃爾夫坦言:“一個健康的身體反應讓它避開疼痛。但美麗思維是一種麻醉藥,它有能力通過麻痹感覺,讓女性更像物體。”
美妝的凝視,詮釋面孔與秩序的關系
在《美貌的神話》之后,許多后來者的著作都詮釋了所謂“美”對女性的規訓以及由此帶來的階級化。
奧地利學者伯娜德·維根斯坦在《美妝的凝視》一書中寫道:“柏拉圖關于‘美與善’的理想,激發了從十八世紀一直到今天還在發展的美妝的凝視。這種理想引導了對美妝的凝視技術上的利用,以求將異常正常化,其程度之強,以至于內在化的美的理想,時常反映和激化政治和身體上趨于同質和平庸的做法,甚至是對文化、倫理和種族他者性的消除。”
這段看起來艱澀、讀起來也頗拗口的話,其實已經成為現實。最直觀的呈現,當屬美顏鏡頭下清一色的臉龐。近年來的國產電視劇,常令人有“分不清誰是誰”的感嘆,女主女配清一色的臉型和五官,辨識度確實很低。審美的同質化必然造成平庸化,“分不清誰是誰”就是平庸化的體現。
“美妝的凝視”這個書名詮釋了面孔與秩序的關系。維根斯坦認為,“美妝”一詞的語源可以追溯到希臘語的“Kosmetikós”,有修飾之意,同時又派生于英語單詞“cosmos”,指的是事物由此開始并被準確地賦于秩序。也就是說,“美妝”早于秩序卻又與秩序相關。凝視不僅是一種雙向互涉的行為,是看與被看的辯證交織,也是一種統治和控制的力量,是主體向他者的欲望之網的一種沉陷。
維根斯坦將“美妝”和“凝視”這兩個定義結合后,認為“美妝的凝視”會引發人的身體內在性和外在性的決裂。它會加速自我重生,同時也建構自身的媒介性。這個定義同樣可以舉例說明:一位女性通過化妝、整容等手段“脫胎換骨”,但也因此重新建構了自我形象,在實際生活中有很大概率實現人生的改變。
但“美妝的凝視”也是一種意識形態。尤其是在消費主義盛行之下,人的身體不但被重新建構,甚至也被物化、被規訓、被操控,甚至被階級化,成為社會等級或階層區分的標準之一。沃爾夫在《美貌的神話》里也指出,對女性美貌的塑造,實際上是在虛構一種女性換取社會機會的“偽自由資本”,讓女性在不平等中通過被凝視換取生存空間。
比如在韓國,化妝簡直已經成為“全民運動”,被上升到禮儀高度,使得化妝從自由變成束縛。這種束縛的本質,是將女性自身置于他人的評價體系中。化妝的“強制性”,離不開商業社會的推波助瀾,它們制造容貌焦慮,使消費者身陷其中。它更將女性徹底物化,以“不化妝見不了人”的思維操控女性。
在維根斯坦看來,無論專制主義還是民主主義,都異化了“美”。所謂“美妝的凝視”,最終也揭示了人類生存于枷鎖之中的殘酷事實。當下世界盛行的醫美、電視真人整容秀節目等,都讓世界變得物化。醫美這種技術手段對人的改造,本質上是技術社會對人的全景凝視和操控規訓。
《美貌的神話》和《美妝的凝視》都印證了一個道理:美貌神話與女性權力進程始終同步,每當女性權力取得突破,試圖撼動社會結構時,社會便會出現新的規訓方式。當下的“美貌神話”,使得女性被強制飾演多個職業角色,包括主婦、事業女性和美女等,也導致巨大消耗。即使女性達到了這個要求,女性雜志、美容和藥品行業、整容行業等又會制造下一個“女性缺陷”,繼而推銷新的產品。對于女性來說,服從“美貌的神話”,意味著無休止的內耗。
“服美役”的可怕之處,在于它限制了女性的權利。真正的權利是“可以選擇化妝,也可以選擇不化妝”“可以追求瘦,但不瘦也不會被嘲笑”……但“美貌的神話”通過“分散女性的精力和時間,讓女性無暇去追求性別平等,男性主導的社會因此得到鞏固和加強”。
沃爾夫在《美貌的神話》里提出了期望:“當一個女性覺得每個女性對待自己身體的做法沒有勉強、沒有脅迫都是她自己的事時,她就贏了。當眾多女性個體讓自己免受美麗經濟影響時,那種經濟就將會開始消失……一旦我們突圍并改變了規則,有關自身美貌的意識就不能動搖,讓我們歌頌那種美麗,裝扮它、炫耀它,陶醉于其中”。
畢竟,“粉飾女性面孔以掩蓋其年齡就是抹殺女性的身份、權力和歷史”。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28547號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28547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