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關注
2025-09-05 16:19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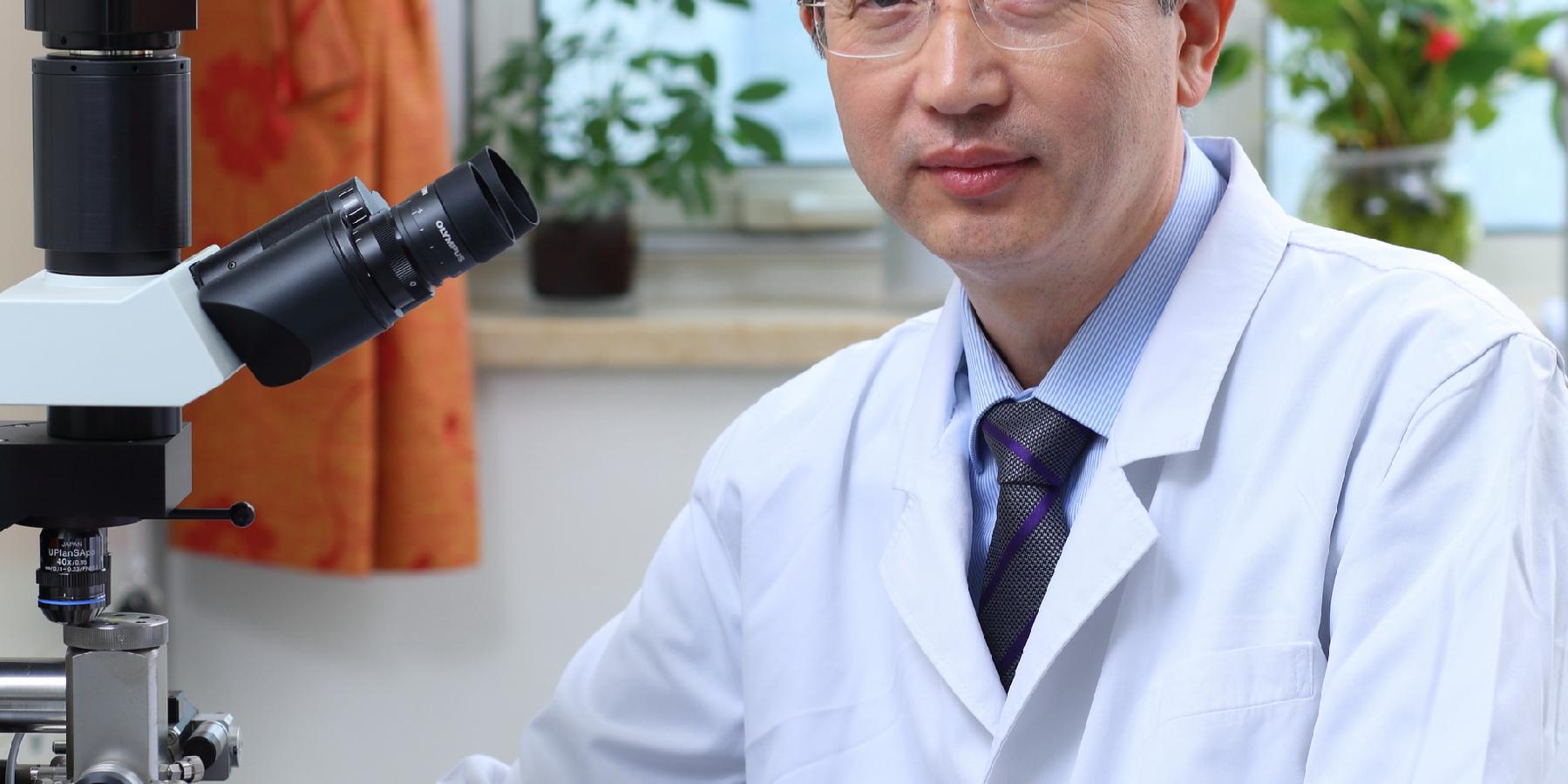
經濟觀察報 記者 張鈴
漸凍癥專家樊東升記得他的很多病人。
8月29日,“2025北京榜樣”公布,樊東升第一時間看到了名單,里面有他一位病人的名字:東方絲雨漸凍人罕見病關愛中心聯合創始人、“漸凍勇士”劉繼軍。
這是樊東升第三次有病人進這個榜單了。2012年,身患漸凍癥仍堅持公益事業的設計師王甲被評為“北京榜樣”。2022年,京東集團原副總裁蔡磊也被評為“北京榜樣”,那是樊東升另一個為人熟知的病人。
樊東升是北京大學第三醫院(下稱“北醫三院”)神經內科主任,中國最早開始漸凍癥研究的專家之一。二十多年里,他接診漸凍癥患者逾萬人,建立的漸凍癥患者數據庫有超過5000名患者,是全世界擁有最多漸凍癥患者的醫生。
對經濟觀察報記者說起病人時,樊東升語調柔和,不緊不慢,這也是他出門診時的樣子。坐在病人對面時,除了叮囑他們好好吃飯,好好睡覺,別那么焦慮外,他總會再給一粒“定心丸”,比如“你的情況總體還是好的”,比如“你的病發展沒那么快,沒那么糟糕”......
漸凍癥被稱為“最殘忍的罕見病”,患病后,人會因肌肉萎縮逐漸喪失運動能力,身體像慢慢被凍住,所以患者也被稱作“漸凍人”。除了蔡磊,物理學家霍金、人民英雄勛章獲得者張定宇也都罹患漸凍癥。在1869年被提出并命名后,人類和漸凍癥的斗爭從未停止,至今,現有療法僅能有限延緩疾病進展,無法治愈漸凍癥。大多數“漸凍人”生存期只有3—5年。
在不欺騙患者的前提下,盡量傳遞希望。對瀕臨絕望的人來說,醫生的聲音很輕,力量卻很重。
從走進診室并最終確診開始,患者就成為樊東升戰壕里的新戰友。最近這兩年,樊東升能傳達給戰友們的力量更多了,除了規范化治療和安慰,他可以對越來越多的患者說:我們正在進行新藥臨床試驗,或許你可以入組。
“當把所有治療都用上,效果也不令人滿意時,臨床試驗就給病人帶來新希望。”樊東升說。
尋藥
8月底一個上午,在樊東升牽頭的多學科診療(MDT)門診,一名來自阿塞拜疆的漸凍癥患者對樊東升說,自己很想參與中國的一項新藥臨床試驗。
最近,樊東升接診了不少海外病人,甚至包括來自美國、俄羅斯等國的患者。他告訴記者,許多海外病人前來,是希望加入在北醫三院開展的一項新藥臨床試驗,這款藥由他和清華大學教授賈怡昌及神濟昌華團隊共同研發,今年8月14日剛剛被國家藥監局批準開展臨床試驗。
“為什么外國病人會來?實際上我們這個研究的機制比較清楚,試驗結果很明確。”樊東升說。
科學家早已發現,人體內一旦出現一種被稱為FUS點突變的基因,就會導致非常嚴重的漸凍癥,患者往往在兩年左右迅速去世。十多年前,賈怡昌嘗試將含有FUS點突變的基因敲入小鼠體內,小鼠卻始終不發病。賈怡昌最終發現小鼠體內一種叫Trim72的基因有效阻止了小鼠發病,去除該基因后,小鼠出現了漸凍癥癥狀。
在這一研究基礎上,漸凍癥在研藥物SNUG01誕生了。樊東升全程參與了這款藥的臨床研究。2023年5月,在正式IIT研究(研究者發起的臨床研究)和臨床試驗被批準之前,樊東升為一名病情嚴重到已經不符合臨床試驗入組條件的患者進行了同情給藥。他說:“按當時的疾病發展情況,患者可能兩三個月就不行了。現在,兩年多過去了,他還存活著。”
經濟觀察報了解到,目前同時有近10項漸凍癥新藥臨床試驗在北醫三院開展,其中有跨國藥企在中國開展的全球多中心研究,也有中國藥企自主研發藥物的臨床試驗,這些試驗幾乎都由樊東升牽頭。這些在研藥物中,既有中藥,也有小分子藥物,還有基因治療和干細胞治療藥物。
越來越多的新藥研究正為“漸凍人”帶來解凍希望。但在數年前,這種熱鬧是難以想象的。
十幾年前,北醫三院還沒有開展過任何漸凍癥新藥臨床試驗。2014年,“冰桶挑戰”公益行動讓漸凍癥被很多人了解,但中國漸凍癥新藥研發依然很少。2019年,蔡磊確診漸凍癥,這之后幾年,他參與推動了一些新藥管線向漸凍癥的傾斜,一些原本不做漸凍癥研究的科學家也把目光投向這里。
在全球,新藥研發是一件公認極高難度的事。相比常見病,漸凍癥新藥的研發難度還會指數級上升。過去數十年,在人類前赴后繼的漸凍癥攻堅戰中,只有“兩個半”藥物順利誕生,一個是賽諾菲的利魯唑,一個是日本三菱制藥的依達拉奉,此外還有渤健的只對2%病人有效的托夫生注射液。
無數制藥公司、科學家的嘗試已經以失敗告終。從概率上講,當前在研新藥最悲觀的結局可能是,沒有一款能順利擺上藥架。
但樊東升不這么認為。他注意到,經過長期努力,神經退行疾病研究正迎來突破期,已經有藥物能真正延緩老年癡呆癥發展。漸凍癥比老年癡呆癥進展更快,在臨床試驗中更易觀察到用藥差別,這意味著可以用更少的研發投入更快完成試驗。疊加政策偏向、資本投入,漸凍癥新藥突破是很可能出現的。
幾乎和蔡磊的大聲疾呼同時,中國政府將更多注意力投向了罕見病,推出一系列對罕見病藥物評審審批和支付有利的政策,這讓資本和企業更愿挑戰漸凍癥新藥這種高難度、高風險的領域。
中國漸凍癥新藥研究起步比歐美晚至少十年,不過,龐大的人口基數給罕見病臨床試驗帶來了獨特優勢。漸凍癥全球患病率僅約4.5/10萬,在歐美,由于病人少,漸凍癥新藥研究開展困難,英國制藥巨頭葛蘭素史克就曾有兩項漸凍癥新藥臨床因受試者不足被迫終止。中國約有20多萬名漸凍癥患者,這個數字還在逐年增長,這讓中國醫生能更從容地為每種藥物找到優質的受試者。
樊東升介紹,為應對入組難問題,歐美藥企不得不進行“平臺試驗”,像共享單車那樣去共享對照組。比如,5個臨床試驗原本各需100例實驗組和100例對照組,共需1000個病人,在“平臺試驗”上,它們將使用同一個對照組,只需要600個病人即可。
共享對照組讓臨床試驗得以盡多開展,但用這種辦法研究不同機制新藥的準確性不高。樊東升說,對于科學家和技術人員而言,漸凍癥或許只是一種疾病,他們只需要醫生為其招募一定數量的病人入組就行了。但對醫生而言,病人和病人千差萬別。
“什么試驗用什么樣的病人,是有講究的。”樊東升說,漸凍癥致病原因不清,異質性很強,這意味著有的藥物也許對這個病人有效,對那個病人就無效了。到底什么病人最適合某個組,依賴醫生的專業判斷。
有的藥和炎癥機制有關,樊東升就會挑選對免疫反應更明顯的年輕患者;有的藥主要對大腦起作用,對脊髓作用較小,他就會找腦損害較重、肌肉萎縮較輕的患者;有的藥主要針對周圍神經,肌肉萎縮較重的病人就會更適合參與試驗。
疾病的復雜,讓病人和醫生的價值在新藥研發中凸顯出來。精準入組最直接的結果是,臨床試驗的陽性率可能被提高,這意味著臨床試驗的成功率很大程度上增加了。
病人,戰友
每位病人入組前,樊東升都會交代:藥物還在研發,有效沒效還不知道;臨床試驗隨機雙盲,可能用的是安慰劑。
他也會強調,即使如此,入組也有意義:在試驗中,病人可以得到醫生對呼吸、營養的密切管理,這至關重要。另外,藥物一旦被證明有效,即使是安慰組病人也有機會在藥物上市前用藥。
每年,樊東升會為至少500個新病人下漸凍癥診斷。很多醫學同行在碰到疑似患者時都會說:“到北醫三院再看看,一是最后拍板,二是看那兒有沒有新治療手段。”
從全國各地來的“漸凍人”不斷涌向樊東升的門診,他們問得最多的就是,有新藥嗎?能試藥嗎?
8月26日,一位患者家屬在診室門口等候樊東升,“其實我來找醫生,是希望能讓弟弟試藥,可惜醫生說我弟弟的呼吸、肺功能情況已經達不到入組條件了。我們都很想參加臨床試驗,起碼能有生的希望”。
許多人把漸凍癥視為絕癥,把確診等同于“判刑”。樊東升說,醫生不能因為病人怕就不下診斷,不診斷就無法治療,這會讓病人的身體機能像自由落體一樣掉下來。
“不是每個病人都是存活3到5年,現在生存5年、10年、20年的病人很多,每個病人都有好的一面。”樊東升說,得病是事實,但強調好的一面能給病人建立信心,做好早期治療很可能獲得較長生存期。缺乏經驗的醫生會認為確診就無解了,說不出每個病人有什么不同,樊東升會把有根據的好消息挑揀出來,給病人抓得住的希望。
病人的離開,是漸凍癥醫生不得不面對的遺憾。樊東升更愿意去看遺憾的另一面,越來越多病人成為“漸凍癥斗士”,和他保持長期聯系:劉繼軍患病19年了,通過良好的康復和照料,他經常能戴上呼吸機、坐著輪椅出門轉轉,看看云彩和鮮花,西安病人張紅帶病生存超過20年,王甲確診也快20年了,還有很多生存超過10年的病人。
這些病人在自助之外,還幫助著其他病友和人群:
劉繼軍和妻子王金環創辦了東方絲雨漸凍癥關愛中心,為病友爭取了許多政府政策和醫療康復資源,給困難家庭提供呼吸機和免費藥品,還代表中國和國際病友交流;
南通籍舞者葛敏在確診后成為漸凍癥公益者,她把病友寫的東西集結為兩冊《因為愛,所以堅持》,每次出版,樊東升都會專門寫序;王甲靠眼控儀寫完20萬字自傳激勵病友對抗病魔,還用稿費成立“王甲漸凍人關愛基金”;
曾在北大青鳥擔任高管的“漸凍人”張紅,在陜西成立漸凍人互助協會、組織病友活動,還給希望小學捐款......
在眾多與漸凍癥抗爭的病人中,蔡磊是走得尤其遠的那一個。除了公益活動,他還在推動漸凍癥藥物研究中起了巨大作用。
蔡磊的分型屬于連枷臂綜合征,這種分型原本可以有較長生存期,但他的進展卻比樊東升預料中更快。“他特別拼,我們會讓病人好好休息,但他全身心投入漸凍癥事業,這對病情不利。”樊東升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哲學,我尊重他。”
2023年7月,樊東升和中國科學院藥物所教授高召兵、清華大學教授賈怡昌聯合研究團隊在《細胞研究》發表封面文章,介紹漸凍癥研究最新發現。樊東升建議用蔡磊的個人照作為雜志封面,在那張照片中,蔡磊昂起頭站在金色的荒漠下,迎向太陽光的方向。由于雜志不接受真人肖像,這款封面沒被采用。

“我們這樣做是想向蔡磊致敬。”樊東升說,蔡磊做了很多工作,尤其是成功呼吁上千名病人同意病逝后捐獻遺體,這在中國文化中非常難得。作為醫生,要和剛確診的病人提遺體捐獻話題,他總是難以開口。病人確診后就離開了醫院,往往在家中度過最后時刻,沒有和醫生表達捐獻意愿的機會。
大腦和神經系統組織對科學研究至關重要,科學家可以嘗試通過遺體標本追溯疾病源頭。長期以來,中國科學家只能在老鼠身上做基礎研究,動物和人之間隔著的巨大距離,會制約科學研究發展和新藥研制。很長一段時間,樊東升只遇到過一個捐獻遺體的病人,那是北師大一位教授。現在短短幾年間,已有超過10位“漸凍人”完成了遺體捐獻,成為珍貴的科研資源。
患病后,蔡磊很快意識到患者數據庫的缺乏,是制約漸凍癥疾病研究和新藥研發的重要因素。確診一個月后,他找到樊東升,說想做一個漸凍癥患者的大數據平臺。
這和樊東升多年的心愿不謀而合。做漸凍癥研究頭幾年,醫院沒有電腦系統,病人一離開醫院,數據就消失在人海中。20年前,樊東升找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設計了一套數據庫體系,此后20年里收集到超過5000名漸凍癥患者數據,成為迄今世界上最大的單中心漸凍癥數據與樣本庫。不過,由于隨訪困難,這些數據不夠動態,不少患者逐漸和他失去聯系。
作為互聯網老兵的蔡磊,在樊東升的幫助下建立起一個全新數據平臺,所有患者可通過平臺自主上傳病情信息,實時更新用藥效果和病程進展。一兩年內,這個平臺就收集到了上萬個真實數據,這是樊東升過去20年收集數據的兩倍。樊東升對這些數據做過初步分析,和醫院掌握的數據情況基本一致。
“最直觀的價值是,只要在這個平臺發布臨床試驗信息,大家都來報名了,入組速度非常快。”樊東升說。

找希望
樊東升出身于醫學世家,爺爺、父親都是醫生。1984年,他畢業于第三軍醫大學(現陸軍軍醫大學)醫療系,成為一名神經內科醫生。
選擇神內,是樊東升覺得與大腦相關的醫學很燒腦,也很酷。不過,20世紀80年代針對神經免疫類疾病治療手段的匱乏,很快讓他意識到現實的殘酷。1987年,他選擇進入北醫三院神經內科,成為那里的第一批碩士研究生,師從神經醫學專家康德瑄。
北醫三院是骨科很強勢的醫院,收治從全國各地來看頸椎的病人。一天,一位骨科醫生在閑聊中說起,他在頸椎病門診發現大量被誤診的病人,做完頸椎病手術后,病人不見好,還繼續加重,最后發現他們其實得的是漸凍癥。這位醫生對康德瑄和樊東升說:“能不能幫我鑒別開來,在手術前就告訴我那該是你們的病人?”
原來,頸椎病和漸凍癥會有一些共有癥狀,比如肌萎縮、上肢下肢麻木僵硬。當時全球范圍內都缺乏漸凍癥的診斷標準,能識別它的醫生很少,一些患者在做完頸椎手術后,反而出現說話不清、吞咽困難的癥狀。
在康德瑄的建議下,樊東升開始尋找線索。在遍尋北京市各個圖書館后,他發現一篇以色列文獻中提到可通過胸段的椎旁肌區分頸椎病和漸凍癥,因為前者的胸段很少出現退行性病變。
這給了樊東升啟發。不過,只有較晚期的漸凍癥患者才會出現胸段病變,這種方法難以用于早期診斷。經過一番研究和思考,樊東升想到,脖子上的胸鎖乳突肌或許是更好的“鑰匙”——它不會被頸椎病影響,但漸凍癥患者此部位的肌電圖會有明顯反應。
答案就這樣被找到了。樊東升發表在碩士期間的這篇論文,獲得了1995年衛生部科技進步獎。通過胸鎖乳突肌診斷漸凍癥的準確率在98%以上,后來被納入中國漸凍癥診斷標準。直到現在,骨科大夫做手術都會非常謹慎,會讓神經科提前參與鑒別,這避免了讓很多病人花幾萬元做完手術反而病情加重。
這次經歷也讓樊東升找到職業信條:科研應該是為解決臨床問題而做的,應該給病人帶來好處,這是醫生價值體現的重要來源。
從二十多年前開始,樊東升就主要接診漸凍癥患者。現在,在他的帶動下,北醫三院神經內科有約四分之一醫生參與到了漸凍癥工作中,許多研究生專門研究這種病,畢業后又留在了這里。
北醫三院是國家神經系統疾病醫療質量控制中心運動神經元病工作組組長單位,因此,樊東升的一個重要任務是定期培訓全國專家,使診斷趨向同質化,讓更多“漸凍人”能在當地得到較準確的早期診斷和治療。這種培訓也為漸凍癥新藥臨床研究培養了人才,因為如果醫生搞不清楚診斷,把被誤診的患者納入臨床試驗,會影響試驗的準確性。
現在,樊東升每周出兩次門診,一次普通門診,一次多學科會診,他要將診斷盡可能精準到各種不同亞型,避免診斷不確帶給患者精神惶恐和治療貽誤,同時努力探尋針對這個世紀難病的治療方法。

在為《因為愛,所以堅持》作序時,樊東升寫道:“于我,(走進診室的)是又一位不幸罹病的患者;而于患者,則是人生旅途上一個猝不及防的拐角......成為漸凍癥研究者是一項多么奢侈而沉重的幸遇。”
經濟觀察報記者問樊東升,如果有一天漸凍癥被攻克,或者有很好的藥物出現,你還想做些什么?
“我這一輩子就想做這一件事(攻克漸凍癥),沒有別的了。”聽到這個問題,樊東升笑了起來,他覺得未來5到10年里,找到一些對部分漸凍癥有效的藥物,讓患者病情得到很好的控制,病情在3年、5年甚至10年里變化不太大,不是不可實現的夢想。在他的構想里,未來漸凍癥會被細分成很多不同的亞型,患者可以根據亞型來選擇最適合的藥。就像托夫生注射液能對2%的亞型有效,下一個藥可能就會對另外某種亞型有效,當一個個新藥出現時,醫生可用的武器就越來越多了。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28547號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28547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