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關注
2025-08-23 15:18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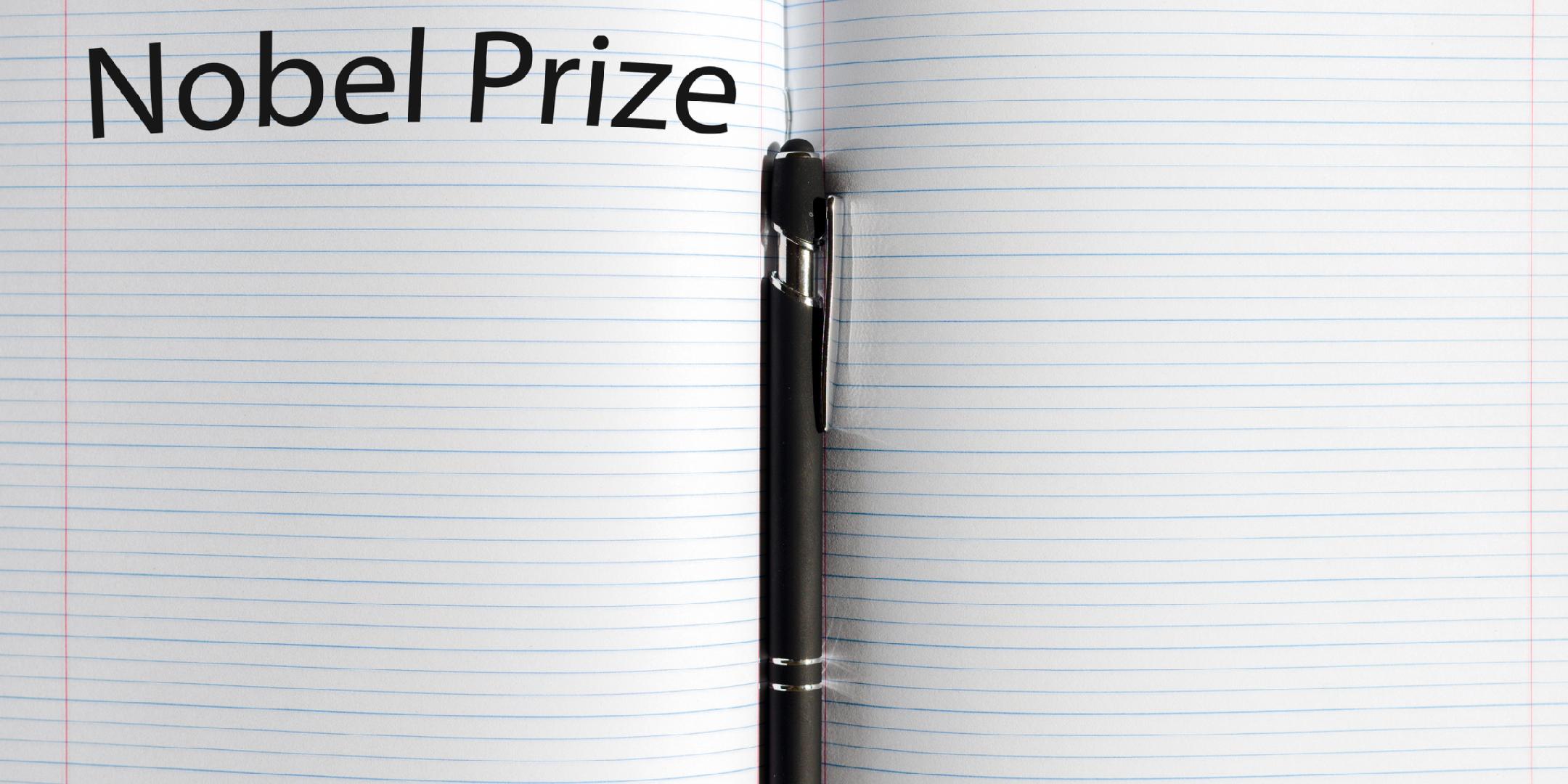
文/云也退
2019年,一個長著一副吹胡子瞪眼表情的男人,被授予了諾貝爾文學獎。作為作家,此人以壞脾氣、愛挑釁人著稱,22歲那年,他就寫了一個劇本叫《罵觀眾》。劇中人上臺來就罵觀眾,得罵他們對舞臺有錯誤的預期,罵戲劇的套路又老又過時。演員滔滔不絕,魔咒一樣的詞語在臺上翻天。
這個作家一炮而紅,他就是彼得·漢德克,奧地利人。《罵觀眾》問世的六年后,他被授予了一個文學獎,此獎全名叫“格哈德·豪普特曼獎”。格哈德·豪普特曼,是德國19世紀至20世紀之交的一位戲劇大家,曾榮獲1912年的諾貝爾文學獎。
雖然漢德克以激進姿態躍入了公眾的視野,可是文學獎及時“籠絡”了他。對于所有和官方有關的東西,漢德克一向鄙夷,消極態度延伸到了大眾,哪怕是買他單、買他入場票的大眾,也能感受到他的看不起。即便如此,漢德克領官方和民間的獎時并無什么障礙,他不會說頒獎方的好話,但也不會拒絕領獎,他似乎認為,人們本就該對他這樣的人物存有虧欠心。
德語世界的文學獎真是不少,而獲獎的常客都借此獲得了國際知名度。2004年,諾貝爾文學獎發給了另一個奧地利作家,埃爾弗里德·耶利內克,此人的爭議性比漢德克猶有過之,筆下的故事情節更加驚悚,對常規風俗的挑釁更為徹底。她在1980年代初寫出的小說《鋼琴教師》,描寫一個學鋼琴的少女如何興致勃勃地自殘,欣然盼望被強奸,等等。保守媒體上一片討伐,書的銷量居高不下,她之前寫的劇本也獲得了更多劇院的青睞。
《鋼琴教師》在1984年拿到一份金額非常高的文學獎金。耶利內克的虛榮大起,她瀏覽那些對她各種嘲諷的報道,更加堅定地認為,自己站在奧地利人的對立面,同時為自己的戲還能繼續上演、書被議論紛紛而驕傲。她繼續寫新作,尤其是1989年出版的《情欲》,充滿了讓人愕然的挖苦話。男人和女人在一起,就為了一直提取她里面的東西——“他看著報紙,從長長的親吻中拉過妻子,猛地一下砸開了她”,“他覺得這是個自樂商店,是讓孩子們成為生意人的商店。在這里人們可以毫無顧忌地小便。”《情欲》就像一個人來人往的客廳,電視柜里持續播放著一盤色情錄像帶。
在授予耶利內克諾獎的決定做出時,一個瑞典學院的院士憤然退場。他受不了《情欲》這類小說。即便如此,耶利內克比漢德克要有趣一些,漢德克的作品里充滿了牢騷和火氣,然后又讓讀者和觀眾淹沒在一種憤世嫉俗的懷疑,然后是絮絮叨叨的無聊感之中。他們二人都是奧地利人,也都處處針對奧地利人;他們領取一個又一個文學獎,同時依然保持我行我素、漠視榮譽和名聲的態度。
他們二人都生于1940年代,他們有一個本國前輩:托馬斯·伯恩哈德,1931年生,1989年辭世。在脾氣、挑釁性、憤世嫉俗這方面,三人極度地肖似。刻薄是他們共有的愛好,他們不斷地蔑視、嘲諷、抨擊奧地利人,同時屢獲文學獎的青睞,是他們生涯里共有的情形。
但有一點不同:伯恩哈德熱衷在自己大大小小的作品中,反復地、全方位地提及文學獎這回事。他甚至寫了一本書,干脆就叫《我的文學獎》。在書中,他說自己曾拒絕了十個文學獎,可是官方還是受虐狂一般地要給他發獎,為此,他才不惜冒著再次被頒獎“侮辱”的風險,寫了這本嘲諷文學獎的書。
尤利烏斯·卡姆佩獎、海因里希·海涅獎、畢希納獎、格利爾帕爾策文學獎、奧地利國家文學獎……從1960年代以來,上述諸獎就前仆后繼地往伯恩哈德頭上砸來,只聽他鼻子眼里“哼”了一聲:“誰是尤利烏斯·卡姆佩?維也納沒有人知道;海因里希·海涅何許人也?維也納許多人也不知道。”他說,文化名人的名字,一個個被拿來設立文學獎,這本身就說明大眾不讀書,對文學沒有興趣,否則不需要如此刻意。再有,就是每個頒文學獎的場合,都是老一套的流程,是官僚刷存在感的場所:
我的講話統共沒有超過三分鐘,這時那位部長便怒不可遏地從他的座位上跳了起來,朝我揮舞著拳頭,他其實根本沒有聽到我的話。他氣急敗壞地當著眾人的面罵我是條狗,當即離開大廳,在身后把玻璃門重重的摔回去,致使門玻璃“砰”的一聲變成了一堆碎片……那一伙我稱之為投機之徒的人,緊跟著揚長而去的部長走出大廳,離開之前也都向我示威……
這段描寫,出自伯恩哈德的另一本書《維特根斯坦的侄子》,是一段對頒獎現場的描述,一點都沒有暗諷、比喻之類,完全是白描。伯恩哈德在受獎時說了一段話,完全沒有常規的客套、感謝,而是吐露了厭世情緒,說了“塵世上的一切如此可笑”,說了“國家毫無價值”,說了“人終有一死”。于是部長跳起來了,揮開了拳頭,罵他是不識好歹的狗。
在《我的文學獎》里,伯恩哈德點了這名部長的名字,樹他為大敵。在他看來,頒獎者并不是真心扶掖文學創作,而只是想以文學來給自己、給自己所代表的政府和國家的面上貼金。在頒獎現場,眾目睽睽之下,表達虛無憤世的情緒,在被“集中看見”的情況下揭露官方的虛偽,這固然很出色,但是之后,獎繼續如同斗氣一般地授予他,“繼續接招吧”——作家和公權力就以這種有點滑稽的方式展開纏斗,越斗還越是彼此難離了。
伯恩哈德的反國家立場,源于他對奧地利現代歷史的看法。1918年一戰接近尾聲時,哈布斯堡王國崩潰,奧地利沒了皇帝,進入共和狀態,和德國的魏瑪共和一樣,奧地利的共和時期,政局混亂,經濟危機的頻繁折磨令人不堪忍受,于是,當希特勒的納粹黨在德國興起,帶動德國強盛時,奧地利出現了一大批擁護者,他們期待靠攏德國,甚至期待納粹盡快來接管維也納。
伯恩哈德的童年正逢這個時期。希特勒1938年來到維也納,受到歡迎,奧地利并入“第三帝國”,它的人口僅占帝國的1/10,但是,整個帝國境內近半數集中營,都設在了奧地利。等到二戰結束,歐洲的法西斯勢力崩潰,德國受到了嚴懲,但奧地利作為一個重要“幫兇”卻被放過了。奧地利用納粹的方式迫害猶太人,排斥那些戰時流亡的作家、藝術家,這些劣跡,在戰后沒有得到清算。不僅如此,奧地利境內幸存下來的猶太人,在戰后還蒙受了新的遷怒:他們被指責為引來災難的人——如果沒有他們,也就根本不會有過去六年的戰爭。
對此,敏銳的文化人拒絕不置一詞。伯恩哈德沖在了最前面,他不停地責罵奧地利人不能正視過去,責罵他們上下一心的偽善、保守、蓄意的健忘。他的戲劇和小說里,有大量瘋癲、亂倫,以及自殺的情節,他筆下沒有善言美句,忿恨的情緒彌漫,主人公在肉體和精神上都走投無路。像是小說《波斯女人》中的主角“波斯女人”,被遺棄,最后臥軌;著名的戲劇《英雄廣場》中,主角是一位猶太裔教授,他跳下英雄廣場自殺,以抗議維也納的排猶行為,在納粹覆滅三十多年后,維也納的空氣里依然充滿了對猶太人的惡意。
一如伯恩哈德在一次訪談中所說,他寫作的核心,是對奧地利的矛盾感情:“哈布斯堡帝國的過去塑造了我們,在我這里,也許比在別人那里更加明顯,我用一種對奧地利愛恨交織的方式表現這種塑造。”在《歷代大師》一書中,他是這么“針對”奧地利人的:
奧地利人,作為機會主義者來到這個世上,他們是些膽怯的人,他們靠著隱瞞和忘卻生存。再大的駭人聽聞的政治事件,再大的罪惡,一周之后他們便能忘記……奧地利人也是生就的罪行掩蓋者,奧地利人掩蓋任何一種,哪怕是最卑鄙的罪行,因為如上所述,他們是與生俱來的膽怯的機會主義者。
奧地利讀者、觀眾對此的反應如何呢?假如他們給的掌聲不夠,那么,一個個文學獎紛至沓來,也給了伯恩哈德以被看到、被接受、被鼓掌的機會。作家深陷一種需要刻意保持的孤膽英雄的“人設”里,他需要更強大的定力,才能頂住榮譽聲名的“腐蝕”,繼續不依不饒、不惜惡毒地批判甚至詛咒奧地利這個國家。
伯恩哈德給耶利內克以及漢德克都樹立了榜樣。陰謀論者會從他們的姿態里解讀出“自我炒作”的味道,從他們博取的名氣里一眼看出投機性。不過,奧地利人似乎不這么認為。官方給的文學獎,不管伯恩哈德如何嘲諷,好像還是順應了民意的。1988年11月,戲劇《英雄廣場》在克勞斯·派曼的執導下上演,當時的奧地利總統庫爾特·瓦爾德海姆(之前他還當過十年的聯合國秘書長,1982年被授予“聯合國和平獎”)被指名道姓地罵,他的前納粹分子的身份被揭露出來。這部戲,是在維也納最古老的城堡劇院正式上演的,劇院由國家出資運營,內容卻是聲討國家的罪惡。
瓦爾德海姆是1986年當上奧地利總統的。這件事,也許對步入晚年的伯恩哈德構成了刺激。1989年2月12日,作家離開了人世。不久后,當《英雄廣場》再度上演時,那些被伯恩哈德罵作“迄今為止總是踐踏我”的奧地利同胞,給了首演式長達40分鐘的歡呼。他們都來看這出痛罵國家、痛罵全社會的戲,演出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漢堡媒體上的一條評語說得很到位:“沒錯,伯恩哈德是奧地利最尖銳的現實主義者,他的每一次爭端也是他的勝利。”伯恩哈德曾諷刺奧地利把國家獎頒給他,是“捐棄前嫌,徹底地與我和好”,那么《英雄廣場》的演出,大概算是真正的修好。奧地利人民,真可謂一些罵得起挨得起的“響當當的銅豌豆”。在他們心里,民族尊嚴之類的東西不是“不可侮辱”的,至少不是那么容易被侮辱的。若要給伯恩哈德一個真正的、“國民作家”級的嘉評,不妨就這么寫:他用他幾十年如一日的批評,有時是近乎無理的詛咒,驗證了奧地利人神經的強大和心智的成熟。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28547號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28547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