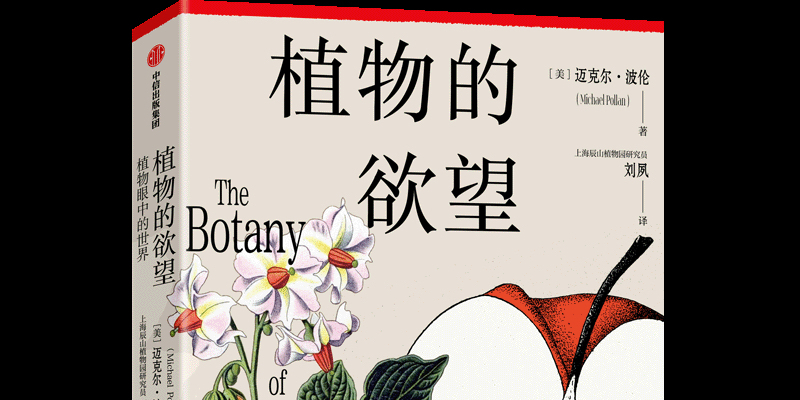
有沒有一種可能,植物在“利用”我們?
綠蘿,這是一種生命力極其頑強的植物。它沿著欄桿瘋長的氣根,像無數只試探的手;新抽的藤蔓精準地繞過防盜網,直奔窗外的陽光;葉子大而油亮,四季常青。你有沒有想過,這真的是人們“養”的植物嗎?還是說,它只是借人的陽臺,續寫自己的基因,完成一項早有預謀的生存計劃?
這個念頭并非空穴來風。在《植物的欲望》一書里,作者邁克爾?波倫拋出了一個類似的視角:我們總以為自己是自然的主宰,卻可能只是植物演化劇本里的關鍵配角。
邁克爾?波倫是《紐約時報》暢銷書作者,2010年被《時代》雜志評為“全球100位最具影響力人物”之一。他的作品多次獲得具有“美食界奧斯卡”之稱的詹姆斯?比爾德獎,“飲食覺醒”系列(《雜食者的兩難》《烹》《為食物辯護》《吃的法則》)至今仍是飲食寫作的典范。
這部亞馬遜暢銷23年的植物科普經典、豆瓣8.1分高分之作,現在由上海辰山植物園研究員、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博士劉夙帶來全新譯本!
在《植物的欲望》里,作者講述四種常見植物——蘋果、郁金香、大麻和馬鈴薯的故事,以及把它們的目標與我們自己的目標聯結在一起的人類欲望。當我們為蘋果的甘甜、郁金香的美艷、大麻的迷醉、馬鈴薯的馴服而傾心時,或許正是這些植物,用千萬年的智慧,精準操控了人類的欲望。
這本書一邊講述著這些植物的社會史,把它們融入我們的故事,一邊對它們所刺激和滿足的四種人類欲望展開了自然史考察。
你“馴化”了植物,還是植物“控制”了你?
傳統認知中,人類是自然的“主體”,植物是被觀察、被利用的“客體”。我們會不假思索地以為馴化是我們在其他物種身上做的一件事。我們說,是我們把微小而有毒的塊莖變成了餐桌上的主食;是我們把不起眼的野花培育成了郁金香;是我們通過人工選擇,讓蘋果從酸澀變得甘甜。
但波倫在書中反問:萬一這其實不過是一種自我陶醉的傲慢怎么辦?
物種馴化似乎代表了征服自然的力量,但這種特別的舞蹈需要兩方參與才跳得下去。很多動植物都拒絕了。蘋果則是選擇了接受邀請。
波倫說,蘋果是自己故事的主人公。
野生蘋果的種子落在地上、長出果樹,結出的果子往往酸澀到“讓松鼠倒牙,讓松鴉尖叫”。對蘋果樹真正的馴化,是從中國人發明嫁接術開始的。在18世紀的美國,糖是非常稀缺的。人們為了得到這份甜,從優良母株上砍下枝條,嵌進另一棵樹的樹干,讓美味得以復制。
可這恰恰中了蘋果的“圈套”:人類為了持續獲得甘甜,看似是人類“掌控”了蘋果的品質,實則是蘋果利用人類對“可復制的甜”的需求,讓自己的優良基因突破單株壽命的限制,實現跨時空存續。
同樣的,人類對于美的追求,使得人類像蜜蜂一樣被花朵吸引。在17世紀的荷蘭,郁金香引發了一場短暫的集體性癲狂,震撼了整個國家,幾乎摧毀了荷蘭的經濟。
通過花色、對稱性和變化等關于美麗的最基本的原則,花朵提醒其他物種注意到它們的存在和意義。而人類為了留住這份美麗,把它從宮廷帶到花園,從苗圃帶到花店。
對許多花朵來說,如今它們生命中的至愛就是人類。我們的寵愛比其他任何蟲子都能保證它們成功繁衍。
人們參與引燃的郁金香狂熱,對郁金香屬植物來說是不可估量的恩惠。我們以為是自己在栽培郁金香,殊不知,是它用美麗為誘餌,讓人類成了它最忠誠的傳播者。
這就是《植物的欲望》最震撼的洞見——馴化是植物利用人類的“演化智慧”,是它們主動選擇的生存策略。就熊蜂采蜜時幫蘋果傳播了花粉,我們在滿足自己的同時,也成了植物演化的“工具人”。
欲望的博弈:從迷醉到控制,誰在操控誰?
植物對人類欲望的操控,不止于“溫柔的誘惑”。當它們瞄準人類對“迷醉”和“控制”的深層渴求時,這場交易就變得更復雜,也更危險。
人類對超驗感的渴求為另一群植物創造了新機遇。一些發苦的壞植物,其中蘊含著最強大的魔力,可以滿足我們改變意識狀態,甚至改變意識內容的欲望。波倫指出,在英文intoxication(迷醉)這個詞當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另一個隱藏的詞toxic(有毒)。食物和毒藥之間的亮線可能是顯眼的,但毒藥和欲望之間的那條線卻不是這樣的。
我們喝咖啡提神,飲酒精放松,甚至通過極限運動尋求刺激——這些行為本質上都是在“擺弄大腦化學”。而大麻,恰恰演化出了一種能精準對接人類神經系統的物質:大麻素。
科學家還在人類大腦中發現了內源性大麻素,并將其命名為“阿難陀酰胺”。科學家推測,它的作用是幫助我們忍受生活中的災殃,選擇性遺忘痛苦,以便第二天重新開始。波倫說:“這是大腦為了應對人類生存環境給自己造的迷藥。”
農業的本質,是一場“殘暴的簡化”。我們把自然的復雜性縮減成人類能管理的秩序——趕走雜草,只留下馬鈴薯;把它們種成整齊的行列,以為這樣就能掌控收成。
19世紀的愛爾蘭,人們依賴馬鈴薯生存,以為這種“馴服”的作物能帶來安穩。但一場晚疫病襲來,單一品種的馬鈴薯成片腐爛,饑荒奪走了百萬人的生命。波倫在書中嘆息:“農夫總以為自己在控制自然,卻忘了控制本身就是一種虛構。”
現代農業試圖用轉基因技術“徹底馴服”馬鈴薯。抗蟲、耐除草劑的品種被研發出來,可這反而讓馬鈴薯更加適應野外環境。
人類越是想控制,就越發現自己被卷入更深的依賴——我們需要不斷研發新的農藥,需要向種子公司購買專利品種,最終,對控制的欲望,變成了被資本和自然雙重牽制的困局。
我們對自己施加于自然的力量、這力量的正當性和現實性都沒有把握,本來也理應如此。
植物教會我們的事:在“互惠”中重新理解生命
在與其他物種打交道的時候,我們過分夸大了自己的功勞。
我們只是一種協同演化關系中的簽約方。達爾文在《物種起源》里解釋道,人類的欲望所起的作用,與盲目的自然在其他情況下所起的作用一模一樣,都決定了哪些個體具有“適應性”。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最終導致了生命新形式的出現。
不過,也別覺得人類在植物面前過于渺小。
“欲望植物學”的踐行者是在把強大的人類驅動力與同樣強大的植物驅動力結合在一起。我們與植物的互動,本質上是自然系統中一場持續千萬年的互惠交易:你提供生存空間,我滿足你的欲望;你塑造我的形態,我影響你的軌跡。
蘋果用甘甜換來了全球種植,人類用味蕾換來了能量;郁金香用美麗換來了永恒的綻放,人類用狂熱換來了審美的滿足;大麻用迷醉換來了跨越大陸的傳播,人類用意識的震顫換來了精神的出口;馬鈴薯用馴服換來了生存的保障,人類用對秩序的追求換來了飽腹的安穩。
把這些植物改而視為自愿與我們建立親密互惠關系的伙伴,也意味著我們會以略有不同的方式打量自己。
每次我們想要最甜的蘋果、最對稱的花、最金黃的薯條時,或許我們沒有意識到,這是我們投下的演化選票。具體來說,馬鈴薯就反映了種它、吃它的人群的價值觀和欲望。有一個品種之所以選育出來,是為了炸制又長又好看的薯條或完美無瑕的圓形薯片。這體現了一種全國性的食物鏈,以及一種喜歡把馬鈴薯進行高度加工的文化。
這場交易里,我們都是為了增進自己的利益,沒有誰是絕對的贏家或輸家。
荷蘭的郁金香狂熱最終泡沫破裂,但郁金香卻借著這場瘋狂,從稀有花卉變成了全球普及的大宗商品;愛爾蘭的馬鈴薯饑荒讓人類意識到單一栽培的危險,但馬鈴薯依然是今天全球第三大糧食作物。植物唯一關心的事——制造更多的自我復制品,目的已經達成。但是,植物雖然通過我們繁盛,它們也為此付出了代價。馴化帶來了豐饒和高產,但也導致了基因的單一化、植物的脆弱和對人類的深度依賴。
在自然的宏大劇本里,我們究竟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在生態危機、氣候變化的背景下,這種協同演化關系該如何重新協商?我們如何建立一種更可持續、更尊重生命多樣性的新型關系?
一起在這本書里尋找答案吧!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28547號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28547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