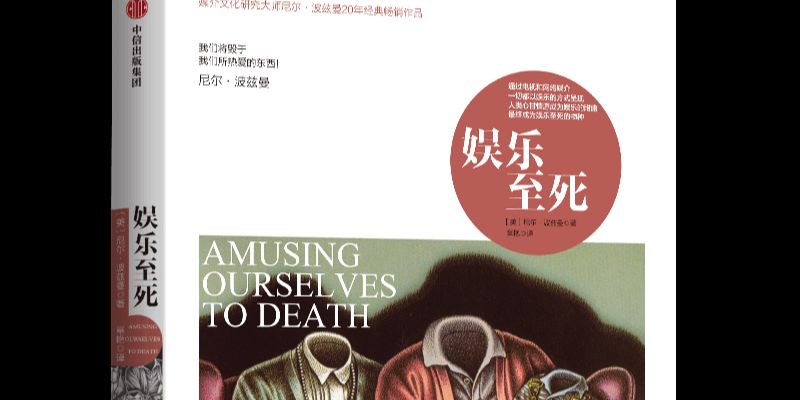
有兩種方法可以讓文化精神枯萎,一種是奧威爾式的——文化成為一個監獄,另一種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為一場滑稽戲。
——尼爾·波茲曼
過去四十年間,媒介領域完成了前所未有的“三級跳”:從廣播電視時代的“接收”,到PC時代的“搜索”,再到如今移動互聯網時代的“推薦”,技術的更新與信息的膨脹共同編織出大眾文化的光鮮圖景。
算法推倒了專業機構與大眾之間的高墻。任何公共話題都能成為爆點,透過屏幕,人們一次次圍觀,一遍遍狂歡。
連最嚴肅的事物都在被攻克。特朗普也許是最具娛樂效應的政治人物,每一天,都有海量用戶在其社媒底下聚集,或大肆吹捧,或百般嘲弄。但放眼全世界,越來越多的政客正在加入這一行列,其原因也很簡單:娛樂化真的有效。
距離尼爾·波茲曼的名著《娛樂至死》出版,已經過去了整整四十個年頭。奧威爾的預言離我們越來越遠,但赫胥黎的預言則在一步步成為現實。事到如今,已有完整的一代人從出生開始,就被拋入了這個“娛樂至死”的時代——哪怕有人已經有意識地與狂歡保持距離。
究竟是我們選擇了娛樂,還是娛樂重塑了我們?我們還有沒有再次選擇的權利?
值此《娛樂至死》出版40周年之際,我們邀請到了華東師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教授、院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吳冠軍老師為本書寫作了一篇書評,談談四十年來的變化,和我們當下的處境。
以下為吳老師的書評全文。
1984年,辯論舞臺上的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面對電視鏡頭金句迭出,贏得全場笑聲。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在其出版于1985年的經典名著《娛樂至死》中,并沒有分析里根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政治學界的關注),而是聚焦里根如何倚靠電視屏幕上的“幽默剪輯”來擊敗對手。波茲曼提醒我們看到:在電視鏡頭下,政治辯論變成長鏡頭特寫、段子金句與聲調管理。這位媒介生態學創始人警告公眾:嚴肅的日常現實會被電視場景化、情境化、娛樂化,而政策討論則會變成脫口秀橋段。
波茲曼深受馬歇爾·麥克盧漢思想的影響,后者的核心學術貢獻,便是提出了“媒介即信息”這個重要命題,亦即,社會總是更多地受到媒介之“性質”的塑造,而不是媒介上的內容。波茲曼則進一步提出,媒介是一門“隱形課程”。我們以為是具體的內容在教壞年輕人,但其實,媒介本身就在“教”壞他們。
如果說技術指的是機器和硬件系統的話,那么,媒介就是技術創造的社會和知識環境。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中提出,“技術中立”本身是一個神話,技術就是意識形態。電視屏幕的默認姿態,便是朝娛樂方向傾斜、追逐最大黏性,若不主動設計“減速帶”,公共領域終將變成綜藝舞臺,政治則變成“演藝事業”(show business)。電視的基本特征是不連續性,而不是連貫性,電視屏幕呈現的是一個支離破碎的世界。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波茲曼已觀察到:書籍正在被電視所取代,沉迷電視屏幕的年輕人無意愿也無能力閱讀任何書。距離《娛樂至死》的出版,四十年過去了,今天的狀況是怎樣的呢?
今天,人們只要一睜眼,觸目可及處皆有屏幕,各種尺寸的屏幕——屏幕已從中產階級的客廳走向每個人的手掌中,乃至眼鏡中。當年波茲曼在時代廣場夜幕中矚目觀瞧并促發他寫作《娛樂至死》的那塊巨屏,今天依然佇立并且分辨率變成了8K。波茲曼曾深有洞見地指出,里根時代競選廣告把復雜政策濃縮進30秒短片。而今日的競選營銷,則直接把政策議題變成“#挑戰話題”或“#表情包梗”——2024年美國總統競選中“八秒競選短片”風靡TikTok,政治綱領被拆成表情包+口播金句,配上快剪鼓點,候選人在八秒內控制你的眼睛。
曾長期擔任真人秀《學徒》主持人的特朗普對鏡頭語言的強大掌控(尤其是獨特的表情管理與身體姿勢、言語風格),使得其政治對手(不管來自共和黨內還是民主黨)紛紛敗下陣來。特朗普每條社媒帖子都具有“爽文”結構與語法,爽點暴擊帶動巨量推送。公眾沉迷不斷刷新的刺激而無暇深究事實。特朗普以高頻社媒轟炸維持議程主導權,也迫使反對者在同一節奏里應戰,于是整個公共領域都被裹挾進“高密度—低深度”的信息閃擊戰,人們的注意力被切成無數碎片,再難完整地追蹤任何復雜議題生長。
2025年1月20日,當選總統特朗普就職典禮尚未散場,便簽署第14172號行政令,要求內政部長將“墨西哥灣”改名為“美洲灣”。該行政令的法律效力尚待國際法確認,但它的傳播效力卻已即時兌現:白宮官方賬號推送特朗普在橢圓形辦公室里揮毫簽下“美洲灣”行政令的20秒短片,配著勁爆鼓點在社媒平臺秒級刷屏,在TikTok當日獲得1200萬播放,相關話題“#GulfOfAmerica”霸榜熱搜。場景化的身體動作進入屏幕即產生情緒價值,司法正當性卻不被看到。政治學界在激烈辯論此舉是否算是構建某種無視法律的“話語主權”抑或“外交霸凌”。波茲曼主義媒介生態學分析視角使我們進一步看到:當特朗普主義政客把該“重命名”行為包裝成了可被不斷轉發、剪輯、配樂的“視覺鉤子”后,該行為的法律爭議很快被徹底覆蓋,沒人再去關注。
波茲曼把媒介視為一種塑造思維的隱形課程,它教人如何思考、如何感受、如何討論公共事務。在《學徒》這個爆款綜藝節目(2004~2017,特朗普于2015年退出)里,特朗普與剪輯師們共同發明了一種三幕式語法:夸張對抗→高光時刻→“You're fired”的瞬間決斷。他隨即把這種語法帶進政治舞臺:政治辯論變身火藥味十足的收視大戰,總統記者會則被壓縮為“十秒金句制造機”。在其第二個總統任期上,特朗普在社媒平臺上自詡“國王”“超人”——這些政客不再假裝進行理性爭論,而是精明地把公共事務轉化為角色扮演。擔任美國的總統,變成了想盡辦法當好一個超級媒體明星;橢圓形辦公室本身亦已變成一款7×24小時在線的“娛樂—政治操作系統”。今年7月17日,《華盛頓郵報》用“世界正被屏幕噎住”這個標題來概括波茲曼四十年前的洞見,驚嘆于這本書的持續穿透力。
媒介的“娛樂至死”邏輯并未過時,反而在平臺算法加持下被推向了極致。
波茲曼關心的并非“媒介好不好”這樣的二元框架下的價值判斷。他關注的是,作為認識論的媒介(media as epistemology)如何悄無聲息地重組人們的世界觀與精神氣質。“媒介即認識論”意味著,我們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媒介,從一開始就有一種組織和改變我們思維方式與認知能力的力量。在生成式AI時代的當下,這個力量比起四十年前更要強大得多。
2025年5月,特朗普在白宮玫瑰園簽下《下架法案》(TAKE IT DOWN Act),這是一部直接針對“深偽”(deep fake)影像的美國聯邦法律,它要求平臺在48小時內下架非自愿的合成影像,并將故意發布者列為重罪 。同年7月20日,特朗普在其本人創建的社交平臺“真相社交”(Truth Social)上轉發了一個視頻短片,在第44秒處顯示特朗普和奧巴馬坐在橢圓形辦公室,隨后三名穿著聯邦調查局夾克、戴著墨鏡的男子抓住奧巴馬并將他拖倒在地,坐在旁邊的特朗普則面露笑容,然后視頻切換到奧巴馬在獄中身穿橙色連身衣獄服。這個特朗普親自轉發的視頻,引發主流媒體一整天的連環辟謠。真相的澄清速度已明顯趕不上謊言的復制速度,深偽技術把“看見即相信”變成“看見也要懷疑”,公共理性被迫在懷疑與疲憊之間搖擺。
媒介即認識論。媒介形態決定民眾如何用什么方式“認識世界”。四十年前波茲曼已擔憂電視會把政治爭論簡化為“誰的形象更迷人”,而深偽技術則讓“形象”本身可被隨意生成、隨時撤換。事實的存在感被稀釋,“現實感”退化為不斷生成與片刻即逝的視覺體驗。以1992年著作《理性公眾》為學界所熟知的美國政治學家羅伯特·夏皮羅,在其2022年文章《謊言、彌天大謊與美國民主》中這樣評論道:“自2016年大選唐納德·特朗普獲選總統以來,美國政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美國歷史上,從未有過如此多的徹頭徹尾的謊言被公開表達,并且在美國政治生活中如此顯眼。”
夏皮羅認為,當下美國政治學中的辯論已經變得可笑:政治學家辯論得面紅耳赤的問題,是“公眾意見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政府政策,以及由于單方面利益的力量,這種影響是否是不平等的”。然而,謊言在電視屏幕與各種社媒平臺肆無忌憚的蔓延,使得“公眾意見”本身被操弄與扭曲。
夏皮羅認為自己早年提出的“理性公眾”概念,已然毫無價值,被當下公眾“關于真相的分歧”有效地瓦解了。
波茲曼四十年前就曾提出:當信息以爆炸性數量溢出,篩選與整理成本將轉嫁給受眾。若無相應的批判技能,信息就像糖衣——甜而空洞。而在出版于2024年的著作《智人之上》里,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仍觀察到一種“天真的信息觀”在盛行:“這種觀點認為,有了足夠多的信息,就能得到真相;有了真相,就能得到力量與智慧。”
持有這種“天真信息觀”的代表人物有貝拉克·奧巴馬、扎克伯格以及雷·庫茲韋爾。這些當代美國政經界精英認為,只要信息足夠多、自由討論時間足夠長,“肯定能讓所有謊言與謬論無所遁形”。谷歌的使命宣言簡潔地表達出了這種天真信息觀:“整合全球信息,使人人皆可訪問并從中受益。”
然而,信息數量堆上去,卻并不意味著就能抵達真相,更不意味著謊言會無所遁形。在《娛樂至死》中,波茲曼深具洞見地提出:“真相的定義,至少有一部分來自傳遞信息的媒介的性質。”而電視屏幕的“性質”,便是具有娛樂化的傾向——它自動奔向娛樂,除非我們主動設計別的可能。
那么,算法支配、深偽橫行的社媒平臺的“性質”呢?如下事實,很有代表性地揭示了該媒介的性質:特朗普將他所創建的那個社媒平臺,稱作“真相社交”。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28547號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28547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