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關注
2025-08-21 16:1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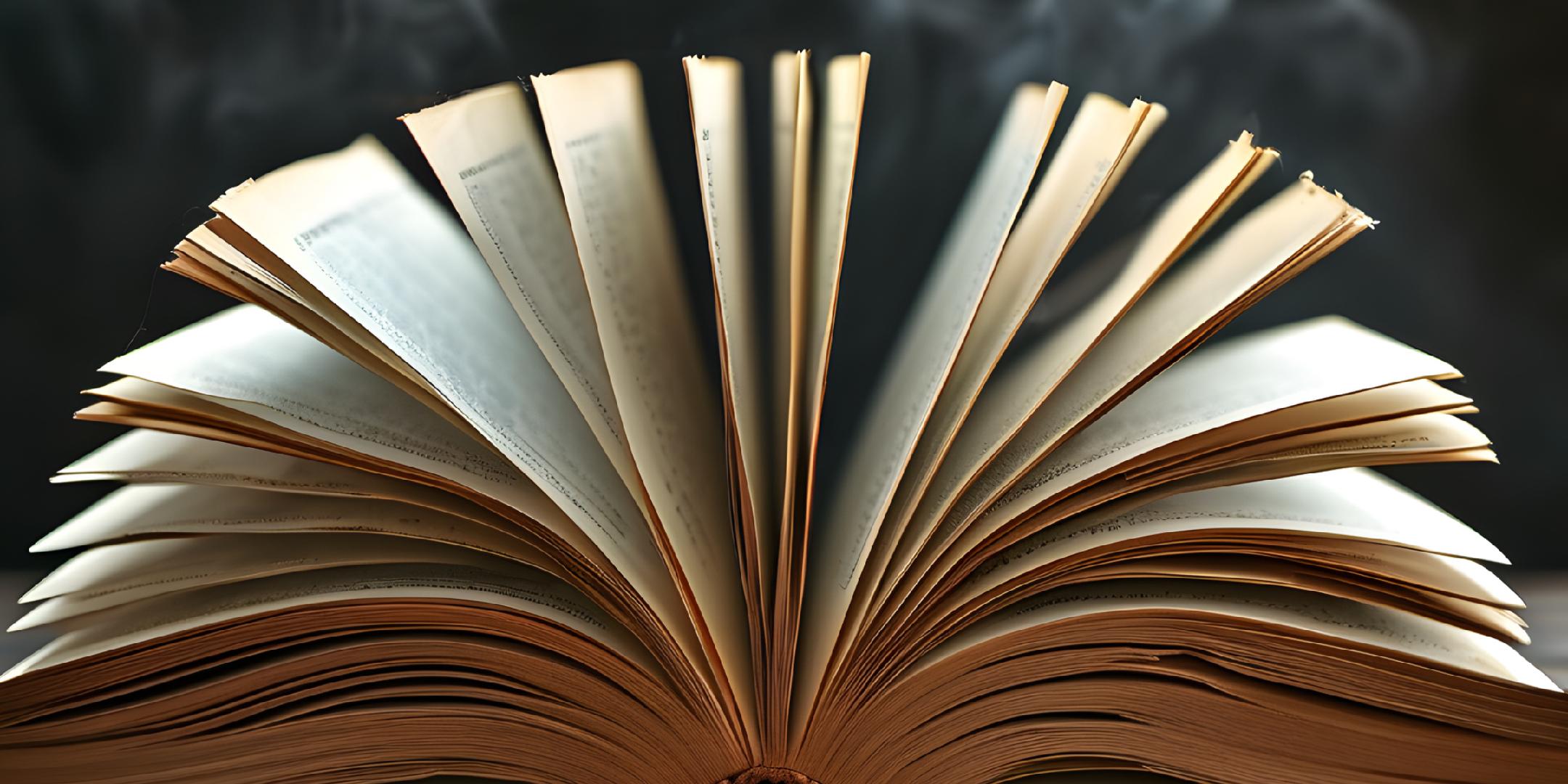
文/劉剛
啟蒙時代的中國法的影響
“休斯夫人號事件”,在西方重啟了“法律東方主義”的話題,從第一種“法律東方主義”——法治文明的中國范,失落為第二種“法律東方主義”——應當被馴服的野蠻。
溯源這一話題,就涉及“東法西漸”的歷史脈絡,李棟《東法西漸:19世紀前西方對中國法的記述與評價》一書,將此脈絡——西方人對中國法的認知變遷,劃分了歷史階段來談。
他從古希臘羅馬談起,談到了對東方“賽里斯國”法治的神秘化想象,一直談到1899年英國學者阿拉巴德出版《中國刑法評注》一書,將“東法西漸”分為七個歷史階段,形成了四種“法律東方主義”,主要形成于啟蒙運動和殖民運動兩個時代。
第一種“法律東方主義”以伏爾泰為代表,但他并未讀過《大清律例》,因為該書1810年英譯出版時,伏爾泰已于1778年逝世,可他生前或許經由傳教士對此有所了解,而傳教士等之于《大清律例》也是僅作為一部完備的成文法,罕見于當時歐洲,而有所推崇,故彼等于此,雖未深究,卻也一概認同。
其認同影響了伏爾泰,所以,這位“歐洲的孔夫子”確認,中國法的本質,是德政與仁治的一個法律形式,其核心在于用禮制引導司法體系,禮法并用,形成德主刑輔的法治。
因此,在別的國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國,其作用更大,可用以褒獎善行,如以表彰孝悌、忠義,教化人民。這樣的法律具有一種天長地久的穩定性,可以作為永恒不變的秩序象征,此為中華法系的一個核心優勢。伏爾泰在《風俗論》中強調:“中國人最深刻了解、最精心培育、最致力完善的東西是道德與法律”,并盛贊中國法律“四千年一以貫之”。
他將《大清律例》代表的中華法系視為超穩定文明的典范,認為其延續性遠超歐洲法律的頻繁更迭。在《哲學辭典》中,他進一步指出這種穩定性源于法律與倫理的高度融合:“中國人將法律與道德合而為一,使法律成為民族精神的自然延伸”。
伏爾泰借中國法律的連續性,抨擊歐洲因宗教戰爭和君主專制導致的司法混亂。他說,“當歐洲人還在森林中游蕩時,中國人已用法律治理龐大的帝國”,這一對比,旨在呼吁歐洲建立世俗理性的成文法典,取代教會法與封建習慣法的割據狀態。
區別于歐洲宗教法,伏爾泰強調中國法律的世俗性:中國的法律不談死后的懲罰與褒賞;中國人不愿肯定他們所不知道的事。法律僅關注現世公正,依賴理性制度而非神權威懾。
中國法律倫理化,秉承了儒家禮法的普世價值,為宗教籠罩下的歐洲,提供了一種道德先于宗教的治理模式,伏爾泰尤為推崇中國法律以儒家倫理而非宗教教義為基礎,他在《路易十四時代》中指出:中華帝國法律的根本精神是“敬天愛人”,統治者無需借助“神啟”便可實現公正。這一觀點,直接挑戰了歐洲的“君權神授”,主張以世俗倫理替代宗教權威作為立法根基。
因此,中國法律有其深度社會整合功能,普現于秩序構建與民族凝聚力方面,法律通過維護家庭倫理,實現社會整合,成為父權政治倫理型國家典范:兒女孝敬父親是國家的基礎。這種思想在人們心中根深蒂固,把這個幅員廣大的國家組成一個大家庭。法律還具有同化異族的力量,他指出元、清兩代征服者都接受漢法:韃靼人發現戰敗者的法律如此完善,以至他們也遵行這些法律;滿族采用漢族法律后,兩個民族不久后就成為一個民族。這正如他所斷言:中國人在倫理和政治法則方面,堪稱首屈一指。
這樣的認知,當然有其局限。然其局限,并非認知不足,而是想象過度,難免美化之嫌。其理想化敘事來源于傳教士,這使他忽略了《大清律例》的嚴刑峻法,如凌遲、株連等,以及司法腐敗的現實,更忽略了滿漢異法、旗人特權等制度性不公。對此,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批評伏爾泰“將想象當現實”。
伏爾泰對于中國法律的論述,止于三個重點:一是道德褒獎,如嘉獎善行,在《大清律例》中,表現為“八議”“養親”等條款;二是程序公正,如死刑復核制,死刑需“三復奏”;三是世俗理性,無宗教審判。但他卻忽略了,其實這三點,皇權都能越法干預,更何況律例條款中,70%為刑法,連民事也用刑罰。
伏爾泰所言,以其啟蒙視野下的中國法想象,對歐洲產生了深刻影響。其本質,乃以東方鏡像投射啟蒙理想,其欲以儒家仁政對抗歐洲神權,以科舉文官制取代貴族世襲,以倫理法體系呼喚理性治理,這使他成為了“法律東方主義”的話事人。
盡管其論述因信息所限,而難免有缺陷,但他還是以此推動了歐洲的法典化運動,并且啟發了魁奈以中國為模型的“自然法秩序”的主張,影響了歐洲啟蒙運動對“法治”內涵的重構——法律不僅是懲惡工具,更是塑造公序良俗的文明基石。
第二種“法律東方主義”以孟德斯鳩為代表,他在《論法的精神》中,對中國法的評價,基于其“專制政體論”,以之為中國法的制度根基,且將中國歸為專制政體的典范——“政令之權全出于一國之君”,皇帝不受法律約束,法律僅為統治工具,其核心為“恐怖統治”,對比一下受貴族與教會制衡的歐洲君主制,他指出中國由于缺乏中間權力階層,而無限膨脹了皇權。專制原則下,“刑罰殘酷且隨意,如‘大逆罪’無明確定義,任何對皇帝不敬均可處死”,他特別批判“連坐制”強化集體奴性。然其信息來源,則與伏爾泰有別,其來自商人,而非傳教士。傳教士多與中國士人交往,或侍于皇帝身旁,養尊處優,故于中國文化,有一種神圣化的傾向。而商人不然,逐利而來,獲利而歸,其所遇者亦商人也,彼此摸索,作為外來者,因信息不對稱,難免吃虧,吃虧多了,故飆起妖魔化的印象,反饋于孟德斯鳩,遂為第二種“法律東方主義”的一個直接的信息來源。
同伏爾泰一樣,孟德斯鳩于《大清律例》文本并未涉及,故其批判亦一如伏爾泰,也是出于其認定,而非以其真知。
他將政體分為三類:共和、君主、專制,自認為中國就是專制政體,此由地理條件所決定,法律亦以環境塑造。他說,中國“幅員廣漠”,須以專制維持統一,對比于歐洲小國,中國的地理條件天然就趨于集權,加以炎熱氣候,也使人“器官纖弱,精神懶惰”,致使其法律千年不變。同時,又因其物產豐饒,而減少其對外需求,自成一封閉的體系。
以此形成宜于專制的禮教,使“禮法合一”——禮教即法律,將宗教、法律、道德、禮儀融為一體,禮教代表法律,禮儀代表風俗,以孝道維系專制,故法以“孝”為核心,將子女對父母的孝,擴展為對君主、官吏的順從,成其“家國同構”。
他以“三權分立”為據,反對司法與行政一體化——官員兼理司法,以刑治國,使法律淪為刑具,在其強制下行道德教化,使得法律不成其為法律,道德也不成其為道德,更何況還有凌遲、株連等,這豈不就坐實了法律以“恐懼”為原則?
再說,中國法這一套千年不變,從未發展,盤桓于腦洞,故其對清代“律例并行”一概視而不見,“律”為綱,“例”為目,綱舉目張,應時而變,顯然,他忽視了這一點,以其“法律東方主義”的偏見,將中國法簡化為“停滯的專制模型”。
其認知局限顯而易見,擇其要者,略有二點,其一,為文本缺失,未接觸《大清律例》原文,只知有“律”,不知有“例”,認定“不易”,不見“變易”;其二,語境錯位,以歐洲“三權分立”為標準,否定禮法合一,忽視中國法的內在理性。
孟德斯鳩對中國法的批判,其本質是借中國反思歐洲——以中國法為專制標本,以之警醒路易十四后的法國,此乃專制鏡像中的法律啟蒙,雖有局限,卻開了法律比較的新范式,不但警示了法律與權力的共生關系,強調法律的制衡機制,而且啟示了現代法治的程序正義、罪刑法定、公私法分立等原則,恰源于對“中國法的困境”的反思,以此劃出超越時代的法治文明的底線。
殖民與后殖民主義對中國法的評價
第三種“法律東方主義話語”以小斯當東為代表,他的名字,跟一部“中國刑法典”——《大清律例》相聯系。
這種聯系,使他能針對“海王星號事件”——“海案”,提出恰如其分并行之有效的建議,在東西方法律沖突中,爭取了“禮之用”的方式,其效果,英人甚為滿意,這緣于他掌握了一本秘笈——《大清律例》,使他能夠“知彼知己”。
在夷館里,設立中國公堂,這在當時的廣州,還是第一次,因而,吸引了全球目光——列強虎視眈眈,有樣學樣,小斯在法庭上的成功,引發了法庭外的政治文化的巨大反應。
小斯對《大清律例》的深度求索及其譯解,開辟了不同于中國刑法的另一個法治空間——“禮法并用”的空間,不但為洋人爭取到了與中國國民同法同權的權利,甚至以外賓身份享受了更多禮遇,故由其英譯的《大清律例》,便成為了大英帝國“以華治華”的一件秘密武器,此乃小斯所奉獻于英倫者。
《大清律例》為律例合編體例,分39卷,其譯律文,計436條,分為六部分,涵蓋軍、政、民、刑等領域,例文部分從雍正年間824條,增補至同治朝1892條,其效力漸已凌駕于律上——“有例不用律”。
于是,小斯開始了他的“中國法的表達”——翻譯《大清律例》。其翻譯經由兩案,先譯“六殺”,再解“律例”,稿成,其友巴羅先睹,著《中國紀行》,贊嘆《大清律例》“文字清晰,結構嚴謹,完全可與布萊克斯通的《英國法釋義》相媲美”,期待“在不久的一天,這部中國法典能以英文準確真實地翻譯出來”。
“海案”中,小斯對照兩個版本的《大清律例》,作全本翻譯,1808年,他返回英格蘭,在船上完成了法典翻譯。
1810年3月,小斯英語全譯本《大清律例》正式出版,譯作用了主、副兩個標題,主標題以音譯,副標題用意譯,定其書名為《大清律例;中國刑法典之基本法與補充條例選編》,“西方人終于能夠通過譯文,直接閱讀中國的法律條文了”,在書的扉頁上,小斯用了一整頁的篇幅作“題記”,向他的好友巴羅致謝。
在他之前,18世紀,瓊斯譯印度《摩奴法論》,將其譯為《摩奴法典》(CodeofMenu),其時,英國尚未開展法典化運動的討論,到小斯時期,邊沁倡導英國以成文法來替代普通法,小斯譯《大清律例》,當可視為對邊沁倡導法典化運動的一次支援。
法典化運動,緣起于邊沁對普通法的三重批判。
其一,批判針對普通法的“神秘性”與不確定性。邊沁指出,普通法,依賴法官造法和歷史判例,其本質是“法官的私人意見”,而非明確的公共規則,其模糊性,使民眾無法預知行為的法律后果,違背了法律應有的明確性和可預期性,法律不應當是“不可知”的神秘傳統,而應為理性的“白紙黑字”的成文規則。
其二,批判針對普通法程序的繁瑣性和虛構性。所謂“程序正義”,實為形式主義,徒增其訴訟成本,且扭曲事實真相,故理應廢除其虛構程序,代之以直接陳述案情的簡明規則。
其三,批判針對法律知識的壟斷性與反民主性。普通法以晦澀的拉丁語、法律術語和分散的判例形式存在,故其被律師群體壟斷,這剝奪了公眾的知情權,使法律成為“精英統治工具”,而與功利主義所追求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相背馳。
因此,邊沁以“全面法典化”取代普通法:法典應覆蓋所有法域,以免法官自行裁量;條文用常言書寫,消除歧義;立法以“功利”原則,為法典確立統一性的價值基礎,構建規則體系;法典應公開出版,確保民眾免費獲取,其目的,不是維護傳統或特權,而是實現社會效用最大化;立法權歸于民選議會,法官僅作為“法典的執行者”,以議會權威,切斷司法造法的根源。
恰于此時,小斯譯出《大清律例》,且以“中國刑法典”問世,這就為當時興起的“法典化運動”,提供了一個東方范例——作為法典化系統的一個有用的和實用的“功利性”范例,而被人認為是引入“中國刑法典”以改革本土普通法的邊沁主義者,其譯介的,正是邊沁欲以之取代普通法的一部系統性的“法典”。
適逢其時,許多議員受了小斯譯介的影響,高度評價中國法的法典化、體系性,以推動英國的法典化的立法,但最終,卻以法典化的方向不符合英國法的自由公正的傳統為由,使之在英國本土無疾而終,然其影響,之于歐陸,卻獲得了成功。
小斯“第三種法律東方主義話語”已自成一派,其于“第二種法律東方主義話語”,經歷了從反對到趨同的演變。
其演變,同東印度公司的命運相關,作為東印度公司的代言人,他對中國的看法,基本上代表了公司的立場。后來公司解體,他作為議員,轉向政府立場,對中國的看法也變了,其“折中的中國法律觀”,就被“第二種法律東方主義話語”所遮蔽。
故其“意譯”,頗有政治工具化嫌疑,《大清律例》是一部中國成文法,除刑法外,兼有民法、行政法和訴訟法等內容,但其本身已渾然為一,并無分別,小斯別具只眼,但見刑法,不看其他,故譯為“中國刑法典”,其“改寫”書名,使人先入為主,認為《大清律例》即刑法,中國法典除了刑法無他法。
顯然,此類“民刑混合”特性,強化了“中國法即專制懲罰工具”的“法律東方主義”的敘事方式,其翻譯策略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西方文化的“認知控制權”,為殖民主義開路。
第四種“法律東方主義話語”代表是阿拉巴德(ErnestAlabaster,又譯阿拉巴斯特),其父為英國駐華總法律顧問。他在1899年出版的《中國刑法評注》是繼小斯當東1810年英譯《大清律例》后,西方學界第二部系統研究清代法典的專著。
其于《大清律例》原文及《刑案匯覽》判例之分析,突破了當時西方主流對中國法的偏見,確認了清律的司法理性——“律例互補”機制及其案例更新機制,使法律能“因時制宜”,認為比英國刑事司法“更少武斷性,更令人滿意”,他批評英國刑法僅將殺人罪分為三類,依賴法官自由裁量權,而清律則通過精細區分犯罪情節,如斗毆工具、親屬關系,實現“絕對確定刑”。
故其針對清律“濫用酷刑”一說指出,凌遲等僅用于“十惡”,如謀反,常見的則以絞刑為主,保留全尸。而贖罪,存留養親,秋審復核,表現出“立法嚴厲而司法寬緩”。
他因此而發現了一個制度亮點,即中國法的超前性與文化適配性,形成了基于身份倫理的量刑原則,如清律將宗法倫理轉化為量刑技術,親屬身份直接影響罪責,子女毆父母加重刑罰,父母毆子女可減罪,還有八議制度,官員、賢者犯罪可議減,體現“禮法合一”的治理邏輯,而非西方人理解的“特權腐敗”。
這里面,有個程序正義的隱蔽機制,盡管清律缺乏陪審團和職業律師,但仍有其內在制衡設計:采取會審制度,由刑部—督察院—大理寺三司會審,防止地方官員濫權;采取死刑復核制度,所有死刑都需經由京城刑部復審、皇帝勾決,減少誤判。這些程序,比英國更嚴,謂之“野蠻”,蓋因其未讀懂律例文本。
至于民事刑事化,亦含有一種治理智慧,他談到了清律“以刑統民”的合理性:民事糾紛,以刑罰威懾,是因為基層社會缺乏專業法官,需依靠刑罰權威保障執行效率,但實踐中,通過“調處息訟”,如宗族調解,以化解民事沖突,避免濫刑。
其于西法生搬、術語硬套,則一概拒絕。一再提示,慎用西法架構套用《大清律例》,稍有不慎,便“不倫不類”,如“能說流利語言卻長著猴子臉”,以此倡導本土化解讀,忠實于中國法的文化語境,保留其原生語義,開創了中國法研究新路徑。
其法治取向,肯定了中國法的內在邏輯與體系性以及法律分類的精密性,其于《大清律例》“六殺”——故殺、謀殺、斗殺、戲殺、誤殺、過失殺的罪責區分比西法更為精細,“故殺”重在預謀,“斗殺”偏于沖突,不同罪名,刑罰差異化,對主觀動機與客觀效果作綜合考察,而非僅以“故意或過失”二分法。
其言司法實踐,認為《大清律例》看似“嚴刑峻法”,但不僵化,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他以大量案例,證明清代司法的靈活性,如保辜制度,鼓勵加害人積極救治被害人以減刑等。
故其批判法律移植,反對清律西化,以捍衛法律文化的本土適應性,他認為《大清律例》與宗法結構、倫理秩序等高度契合,西法難以替代,如強行引入,會破壞社會固有平衡。主張“中國不應按西方標準變革法律”,因為將西法術語運用于中國法,這樣做非常危險,何謂故殺?難道是謀殺嗎?不是。
其譯清律,不但“律例全譯”,且以“律例互證”,結合《刑案匯覽》的司法案例,深入“律”的實際運作——“例”,而小斯當東譯本,僅譯436條“律文”,忽略1042條“例文”。
小斯當東贊《大清律例》“條理性、清晰性超越亞洲他國”,語言“簡潔如商業用語”,承認其父權制與君主制的社會基礎,如“服從家長權威獲民意支持”,但他同時又認為,中國法混同“民事、政治與禮儀”,未形成獨立的法律體系,表現為等級性司法,如“八議”制度助長特權,執法者常帶頭違法,而且缺乏現代性的“無罪推定”“不可自證其罪”的司法理性原則,故其研究成為英國攫取領事裁判權的法理依據,并助推了武力侵華。
總結一下,此二人者,因其所處時代不同,一處于鴉片戰爭前殖民擴張期,一處于西方治外法權確立后反思期,故其傾心的問題也不一樣。一問向“中國法律野蠻,西方如何接管”?一轉向“中國法律如何適應本土社會”?問題不同,翻譯迥異,一者編譯,刪減律例,為政治服務;一者全譯,尊重原本文化語境。其結果,概言之,一為殖民利益代言人,一為文化相對主義先驅。
總之,其差異乃時代語境下的認知嬗變,其本質為19世紀西方對華立場從“殖民征服”轉向“反思霸權”的縮影。小斯當東代表帝國擴張期,將《大清律例》解構為“他者標本”;而阿拉巴德在殖民既成事實下,以文化相對主義視角對中國法進行再認識,然其保守性也使他忽視了清末中國社會變革的必要。
說到底,西方對清律的解讀,無論小斯當東的“侵略工具論”,還是阿拉巴德的“文化辯護論”,從未脫離權力語境,均如薩義德所言:東方主義始終是西方確立自我優越性的鏡像。
若放到“東法西漸”的大周期上來說,我們發現小斯當東和阿拉巴德經歷了一個循環,當小斯當東向著孟德斯鳩回歸時,阿拉巴德卻回到了伏爾泰,在歷史回音壁上說著啟蒙時代。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9卷,中信出版社)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28547號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28547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