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關注
2025-07-14 15:29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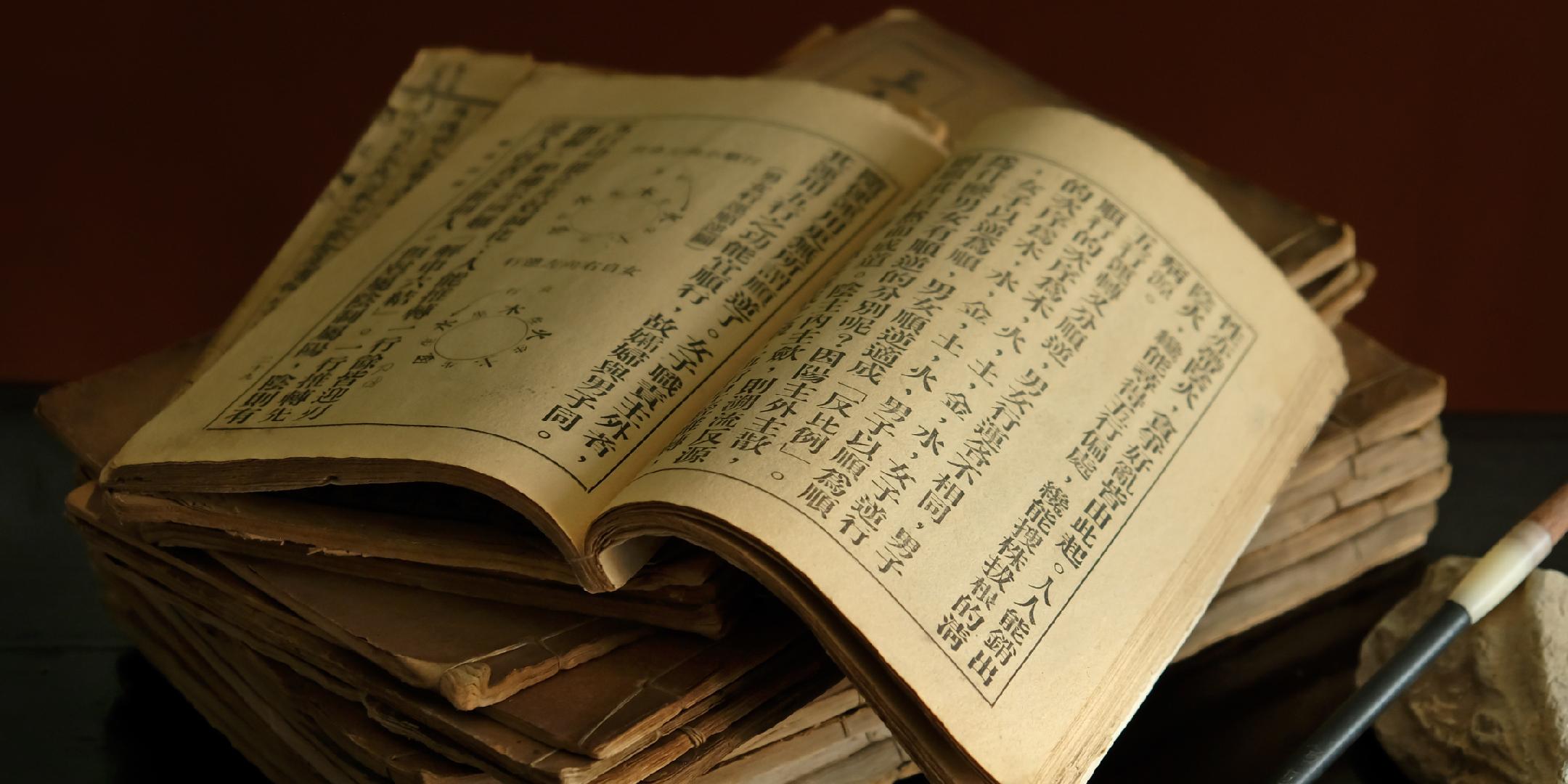
文/李冬君
何以中國長期停滯
“何以中國長期停滯”?或曰“彈性社會”,或曰“超穩定結構”,二說均試圖解釋中國傳統社會何以長期穩定,但其視角、方法論和核心結論卻差異明顯,我們來比較一下。
“彈性社會”理論,將中國傳統社會定義為“早熟而不成熟”的彈性結構,以其多元經濟基礎與復雜控制系統吸收變革能量,表現出“彈性”調整能力,卻難以突破既定框架,其觀察,以動態視角,故其所見,新舊因素并存,沖突與協調交替,展示出階級對立與鄉族互聯互動,政權壓力與紳權轉化相交織,經濟驅動與超經濟強制共同作用于多元經濟(國有、族有、私有)中。
而“超穩定結構”的定義,則基于中國傳統社會——自秦至清的帝制時期,有一種“超穩定系統”,其特點表現為周期性震蕩,如王朝更替、農民起義、外族入侵等動亂雖然頻繁發生,但深層結構穩定,每次動蕩后,社會總能通過系統調節恢復其原有的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結構,農民起義等動亂,反而作為其系統修復的“安全閥”,未能觸動其根本矛盾,因而不會發生質變。
其社會形態由三個子系統耦合而成,其一,為政治結構,由中央集權的官僚體系與皇權專制構成;其二,為經濟結構,以小農經濟為主,由土地私有制與地主—佃農關系構成;其三,為意識形態結構,以儒家倫理如“三綱五常”的核心價值構成。此三者,以其“耦合”形成強關聯,相互強化維持其穩定性。
兩種理論,對于歷史解釋力的側重點也不同。
傅衣凌的“彈性社會”理論,指出其多元結構的韌性,例如,明清社會,雖然出現資本主義萌芽,但因鄉族勢力、官僚體制的上下制約,新因素被“死的拖住活的”,形成彈性往復,而非斷裂。還有在地方與中央的互動中,鄉紳階層協調國家與基層社會的作用,既維護中央集權,又保留地方自治空間,成就彈性的政治基礎。其經濟形態,亦多具兼容性,如“一田多主”制、永佃權等現象,反映土地關系的靈活性,既緩解沖突又固化傳統。
金觀濤的“超穩定結構”說,表現為“系統自我修復”機制,王朝更替,通過重建小農經濟和儒家意識形態,重新恢復舊秩序,如“漢承秦制”,循環不已;還表現為“意識形態固化”和“技術停滯”,儒學與科舉制,排除思想異端,抑制變革動力,重農抑商政策壓制商業資本積累,導致技術發展缺乏社會支持。
對“停滯”與“變遷”的解釋,兩說也有差異。
傅衣凌說是“彈性中的漸變”,他認為,社會雖未質變,但內部卻已持續微調,如租佃關系貨幣化、商業資本滲透,其“彈性”使傳統社會適應外部壓力,使之無法突破原有結構。而金觀濤則認為是“結構鎖定下的循環”,強調系統通過周期性震蕩(如農民起義)消除偏離,回歸原穩態,變革被“吸收”而非積累。
兩說具有互補性,表現為微觀彈性與宏觀穩定的互補,傅衣凌的多元結構說為金觀濤的“超穩定”提供了微觀基礎;還表現為動態調整與系統鎖定的互補,“彈性社會”理論更強調社會內部的能動性,而“超穩定結構說”更強調要突出系統的剛性約束。
“彈性社會”以其微觀透視揭示傳統社會吸收變革能量又囿于傳統規范的矛盾性,突破了“停滯—進步”的二元敘事,而“超穩定結構”,則以宏觀系統模型,解釋了社會結構抗拒質變的深層機制及其結構性鎖定,構成“變與不變”雙重視角。
中國城市的雙重變奏
我們還可以將“兩種類型”的城市——開封型與蘇杭型,放到這“兩種范式”下來解讀,對它們進行一次再認識。
“蘇杭型”城市,具有“彈性社會”的典型性特征——“早熟而不成熟”,自有一番“萌芽”氣象,明清時,曾以工業擴張城市空間,形成經濟主導的“府城+衛星市鎮”格局,而有新舊經濟形態共存、地方自治與中央集權互動的“伸縮性”表現。
然其經濟,雖稱“繁榮”,但依然受制于“超穩定結構”,未能突破其結構性的系統鎖定,如明清以海禁抑制海洋貿易,商業資本始終以農業為“本”,錯失了工業革命的臨門一腳。
而“開封型”城市,則是個“超穩定結構”的典型,其興衰周期,取決于治亂與治水的地緣政治,金、元以降,已失都城地位,但其系統,官僚體系與小農經濟依舊,仍在維系。
其經濟結構單一,明顯“彈性”缺失,不離漕運,固守農本,短于多元土地建制,缺以區域分工形成的市鎮體系。
如果我們對這兩類城市做一下對比分析,就不但可見它們興盛期的動力差異,如蘇杭為市場化的內生增長,而開封則由政治權力主導的外生驅動;還可見衰落時期它們的路徑分化,蘇杭型表現為彈性緩沖下的漸進調整和“適應性停滯”,而開封型則表現為結構鎖定下的系統性崩潰,陷入“失序—重建”循環。
蘇杭型與開封型的分野,基于一方水土對“彈性社會”與“超穩定結構”的選擇,江南選擇“彈性社會”,成就其蘇杭型市鎮,中原傾向于“超穩定結構”,以此造就了開封型都城。
江南與中原,作為兩大核心地理單元,天南地北,成為中國版圖里最重要的兩條歷史地理線及其政治文化景觀。
其差異,固由其天時地利的自然屬性使然,亦與其各自所在的歷史地理線在中華文明的統一性中的分擔相關聯。
中原一線,以秦嶺—淮河分界,據之以封邦建國,改朝換代,堪稱為“一代王朝的生命線”,其范圍,涵蓋黃河中下游流域,核心區域,為關中、河洛之地,以大平原,環以山河。
而江南一線,先以長江中下游,曰吳楚,稱兩江,宋以后,名位東移,移至下游太湖流域,從“六朝古都”到“江南八府”,從白銀時代“中國風”到工業革命的經濟風暴來臨,江南不僅成為全國經濟中心,而且成為全世界的一個經濟中心。
在文化方面,江南一線,亦堪稱“文化中國的底線”,不但在文明的起源上,走在了中原的前面,而且在歷史進程的各個階段中,也步步領先,一直走在了前面,自上古迄于古代,從良渚神權古國到吳越技術霸權,再到楚漢文化對帝國的重塑,江南始終是一條與中原并行的文明軸線,其歷史并非“追趕中原”的被動進程,而是以“技術突破—文化融合—制度創新”的自主演進。
漢朝雖定都長安,但其文化內核深受楚風浸染,經濟命脈依賴江南資源,所謂“漢承秦制”,實為“漢融楚魂”。
尤其魏晉以降,六朝相續,維系中國浮沉,唐宋以來,金元交替,異族入主中原,明清迭代,認同中華一脈,其以江南為底蘊,與之同化,復興國土,再建新王朝,重啟攘夷篇。
縱橫千年,放眼望去,歷史云煙,不過如此。
若就此而言之,亦可謂其為一“超穩定結構”。
舊朝顛覆之后,新朝又開基了,在王朝中國的地基里,“開封”維新,“蘇杭”適之,中原與江南又達成了新統一。
可工業革命的風暴來臨時,卻非如此,雖然伴隨列強入侵,但不是來中國做皇帝,而是來與中國做生意,不要改變中國政權,卻要改變中國的經濟,尤其要改變那個“超穩定結構”。
近代工業革命對中國“超穩定結構”的突破,本質上是外部力量與內部變革共同作用的結果。金觀濤提出的“超穩定結構”認為中國傳統社會通過政治(中央集權)、經濟(小農經濟)、意識形態(儒家學說)三系統的強耦合實現周期性震蕩與修復,而工業革命帶來的技術、經濟與思想的沖擊則突破了這一閉環。
工業革命的“三重機制”,瓦解了“超穩定結構”,其一,經濟先行脫嵌,小農經濟解體,使政治失其物質基礎,使意識形態脫離社會土壤;其二,政治失序反哺經濟,地方割據與軍閥混戰為新經濟因素提供了生存縫隙;其三,士人轉型催化革命,以科學廢科舉,造就新知識分子,以民主廢君主,推動制度革命。
工業革命不僅是技術變革,更是撬動中國“超穩定結構”的歷史杠桿,其突破路徑,以外部沖擊啟動系統震蕩→新經濟因素侵蝕傳統基礎→政治與意識形態被迫轉型→耦合斷裂后進入現代性探索。這一過程,充滿暴力——戰爭、陣痛——社會解體、希望——啟蒙運動,使中國從“超穩定”狀態,轉入“大變革”時代。
工業革命的“洋務”反應
然而,“超穩定結構”解體了,中國并未解體,王朝崩潰了,中國沒有崩潰,而是反彈起來,回應了“民主革命”的巨大的反作用力,非英國式的君主立憲,而是美國式的民主共和。
通過“回應”,我們發現,“超穩定結構”中的“穩定”二字,并非來自這個“結構”的本身,因為,“回應”的反作用力,非由此“結構”發出,故用“結構”的核心三要素——小農經濟、中央集權與儒家學說,均“回應”不了此次的工業革命。
三千年來,改朝換代常有,而工業革命不常有,其三千年等一回,故曰“三千年之巨變也”。
那么,“回應”從哪里來?我們不妨回頭去看中國的另一面,看一下“彈性社會”,就會發現中國的第一“回應”,來自民間社會的“彈性”,來自“資本主義萌芽”對“工業革命”的反應,來自“江南道路”對“英國模式”的轉化效應,不是“開封型”城市的無奈之舉,而是“蘇杭型”城市的驚醒發出了“回應”。
最初的“回應”,便是“洋務”,在中國運動了。
洋務運動,興起于江南,而非中原,是江南“彈性社會”的不屈的反彈,而非“超穩定結構”的強制使然,是“彈性社會”以其多元性和適應性來轉化系統危機,并以其“彈性”的“回應”,生成新的歷史機遇,而非“超穩定結構”的絕處逢生。
19世紀60—90年代,作為近代化的嘗試,洋務運動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民間社會的“彈性”機制,卻又因其未能徹底擺脫“超穩定結構”的制度性束縛,而難以超越被超經濟強制限定的“彈性陷阱”,最終被內外夾擊陷入結構性失衡。
工業革命打破了傳統小農經濟,“洋務”作為新經濟因素,侵入其基礎。對此,官本位的“開封型”城市,已是動彈不得,而民本位的“蘇杭型”城市,則反而趁勢擺脫了“超穩定結構”的強制,對外開放了它的彈性機制,不但兼容“洋務”,而且化為“運動”,使之如巨浪擴展的圈層,一浪接一浪的“內卷”。
這已不是小農經濟的自發性的內卷,而是外來的新經濟因素——“洋務”,深入其中的“運動”所帶來的內卷。
好在“蘇杭型”城市群本身,在其早期工業化的資本主義萌芽中,便已具備了“斯密型動力”,有過“斯密型成長”的經驗,它自身雖未能以技術突破產生工業革命,但它卻深藏了接受工業革命并隨之而“工業化”的潛能,萌芽不死,仍在新生。
可“超穩定性結構”呢?盡管已在瓦解中,卻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即便瓦解,也要一步一步來,帶著“富國強兵”的面具,投奔到“洋務運動”中,邁出了它自救的第一步。
其自救也,以官辦為主,通過創辦軍事工業(如江南制造總局)和民用工業(如輪船招商局),部分引入商股,如招商局就采取“官督商辦”,形成“國有—私有”混合的經濟模式。
其技術引進,帶來新型工業化布局,以上海為中心,帶動周邊“早期工業化”升級,造就江南地區“官廠—民坊”群落。如上海機器織布局紡織機械改良,催生了無錫、南通等地小型紡織工場,這種技術溢出效應,強化了江南市鎮經濟的彈性。
官辦“洋務運動”,雖在江南“彈性社會”的基礎上開展,但其自身“超穩定結構”的殘余還在,導致新舊經濟的共生困境,形成“彈性陷阱”,其官辦收入,多用于軍費開支或官僚消費,而非擴大再生產,如江南制造局年耗銀約百萬兩,但甲午戰爭前,僅造艦40余艘,其效率遠低于日本同期。這種“技術依附性增長”未能轉化為社會財富積累,導致“國富民窮”的失衡格局。
在政治結構上,也出現了地方勢力的彈性擴張,松動了中央集權擰緊的分權螺絲,湘淮軍閥,如曾國藩、李鴻章等,通過主導洋務企業,形成地方財政與軍事自主的“半獨立化”,其“督撫專權”類似“鄉紳協調機制”,可謂對專制的彈性調適。
清廷為防范地方坐大,讓戶部插手各地官辦企業,加劇了中央集權與地方勢力的博弈,導致政策拉鋸,因而屢遭挫敗,如張之洞籌辦盧漢鐵路,受限于戶部撥款,被迫向比利時借款而失其路權,可見“洋務”彈性仍受制于清廷“超穩定結構”。
城鄉一體的工業模式
其于社會方面,江南士紳及其宗族資本,遭遇了工業革命的猛然一擊,也開始了產業與身份的轉型。如南通張謇、無錫榮德生,將地租收入轉投于洋務企業或民辦工業,形成“地主—資本家”的雙重身份,或依托宗族網絡——如榮氏家族的錢莊支持,或建立鄉土權威——如張謇擔任南通自治會長,構建起“企業—社區”一體化模式,延伸了“彈性社會”里的鄉族協調機制。
這種資本轉化路徑,體現了傳統鄉族經濟對“工業化”的彈性適應,如張謇開辦大生紗廠,就依托南通原有的“棉—農網絡”,進一步構建“棉墾—紡織—銷售”一體化產業鏈條。
但是,民族工業興起,未完全取代傳統經濟,而是形成“小農經濟—手工業—近代工業”的混合結構,如無錫榮氏家族的茂新面粉廠與當地農村的麥作經濟形成共生關系:工廠收購本地小麥,農民收入增加后購買機制面粉,形成區域性經濟循環。這種新舊產業的互補性,體現了彈性社會“多元并存”的特征。
基于“彈性生存”原則,勞工階層也在轉化,由破產農民和手工業者轉化為“洋務”工人,如江南制造局,雇工超2000人,但其管理方式,仍是封建工頭制,不但薪資微薄,且無保障,如此勞動關系,提供了底層流動機會,也加劇了階級矛盾。工人來自農民,其彈性生存,表現為保留農村土地作為退路,形成“半工半農”的彈性身份,以“離土不離鄉”的流動模式,化解了工業化初期的資本血腥,但也阻礙了勞工的“階級”意識的覺醒。
還有買辦階層的興起,洋務企業雖說由官來辦,但官家哪有能力真的來辦?怎么辦?解決問題的人,已經準備好了,那就是買辦。買辦不但在官商之間起到緩沖作用,而且充當了“土洋結合”的膠粘劑,以其洋務經驗服務于本土企業,利用外資銀行貸款緩解中國資金短缺,如唐廷樞之于開平煤礦,虞洽卿等融資創辦四明銀行,其買辦性使民族資本與外資形成共生關系,以其“依賴中的獨立”體現了“彈性社會”對外來沖擊的靈活反應。
正是在多元經濟形態的彈性轉換中,在傳統經濟網絡的適應性轉化中,依托于傳統經濟彈性中的多元所有制和地方市場體系,興起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族工業的本土樣式。
從江南絲織業轉型中,可見手工工場與家庭紡織并存,形成“機器生產+家庭代工”的混合模式,延續了彈性社會的“新舊共生”特征,此模式,既開源了原手工業者的技能,又節流了初期資本投入,顯示了經濟彈性對工業化的緩沖作用。
從資金來源看,近代民族工業的原始資本,或依賴地租轉化,或來源于官僚資本,或由外國銀行貸款,這種對傳統勢力和殖民資本的依附,暴露了彈性陷阱下的依附性發展,被“死的拖住活的”糾纏,導致其難以自主地形成獨立的產業體系。
鄉紳階層的資本轉化,不但通過地租積累投資近代工業,而且利用宗族網絡組織勞動力,如招募同鄉工人,以此,延續了彈性社會原來的“地方自治”機制,如此轉化,既緩解了封建經濟解體帶來的社會震蕩,又為工業化提供了本土路徑。
轉化,造就了民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以彈性社會的調和方式,一變“士農工商”的舊格局,讓資產階級認捐政治身份,將工人納入封建行會管理,新舊階層在妥協中磨合。
被制度約束的轉化,在彈性結構的磨合中,已形成路徑依賴,雖以“官督商辦”和“獎勵實業”之舉,來對“超穩定”的政治體制作適應性調整,欲在彈性框架內轉化危機,然而,充其量亦只能緩解其體制壓力,卻難免體制腐敗和主權喪失。
其意識形態,也以有限的包容,將工業化納入儒家倫理,通過“實業救國”之類的話語——如張謇所謂“父教育,母實業”,來調和其價值觀與資本主義的關系,然其工業化,采取工頭制管理,可見其思想彈性的乏力,以新式學堂(如京師同文館)培養技術官僚,既推動變革又受制于科舉廢除后的身份焦慮。
歷史的鏡子,反映了“彈性社會”的限度及其變革困境,純以技術移植難以突破“彈性社會”閾值,技術變革與制度惰性沖突不已,局部彈性與系統鎖定,也成了一個悖論。
江南地區的經濟活力,被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因其主權缺失,反而強化了清廷對列強的財政依賴,為了王朝續命,不惜以關稅抵押外債,形成“越開放越脆弱”的惡性循環。
而傳統的現代性轉化,也在“實業救國”實踐中表明,缺乏產權保護與法治環境,彈性動力很難彈出“現代性”,在“彈性社會”的基礎上,“洋務”受制于“彈性極限”,再怎么“運動”也難以實現歷史性的突破,需要新的“革命動力”的來源。
其來有二,一是經濟彈性崩潰催生政治革命。
民族工業以“彈性社會”為基礎的協調性成長,以其脆弱卻又生生不息的活力,催生了無產階級的人口,催化了資產階級的政治訴求——如立憲運動,為革命提供了階級基礎。
二是思想彈性的瓦解開啟了新文化的啟蒙。
民族工業推動了新的城市化,如上海人口,從1870年20萬,增至1920年200萬,由此催生了市民文化,不斷沖擊儒家倫理的圍城,使“彈性社會”的意識形態功能徹底失靈。
我們由此可見“彈性社會”的歷史辯證法。
洋務運動是“彈性社會”的一次大規模調適,也是其內在矛盾的總爆發,它在經濟上激活多元性卻又因之陷入依附性增長,在政治上釋放地方活力卻加速了中央集權崩塌,在社會上推動階層流動卻未能建立公平秩序而表現為“彈性中的僵化”。
而民族工業崛起,則是“彈性社會”的“最后輝煌”,也是其解體的開端,其彈性滋養,以適應性調和新舊因素,從傳統中轉化出新的生存空間,然又難免彈性陷阱以其新舊共生的糾纏抑制獨立工業體系形成,并導致彈性崩潰,出現經濟依附性危機和階級矛盾激化,終于推動中國從“超穩定”走向社會革命。
這一過程揭示,傳統社會的彈性機制在近代化浪潮中,既展現了文化的柔軟性和歷史的適應性,也暴露了它的根本性局限——唯有打破新舊共生的慣性才能真正實現社會轉型。
(作者近著:《走進宋畫——10—13世紀的中國文藝復興》,北京時代華文書局)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28547號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28547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