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jīng)濟(jì)觀察報(bào) 關(guān)注
2025-07-12 08:1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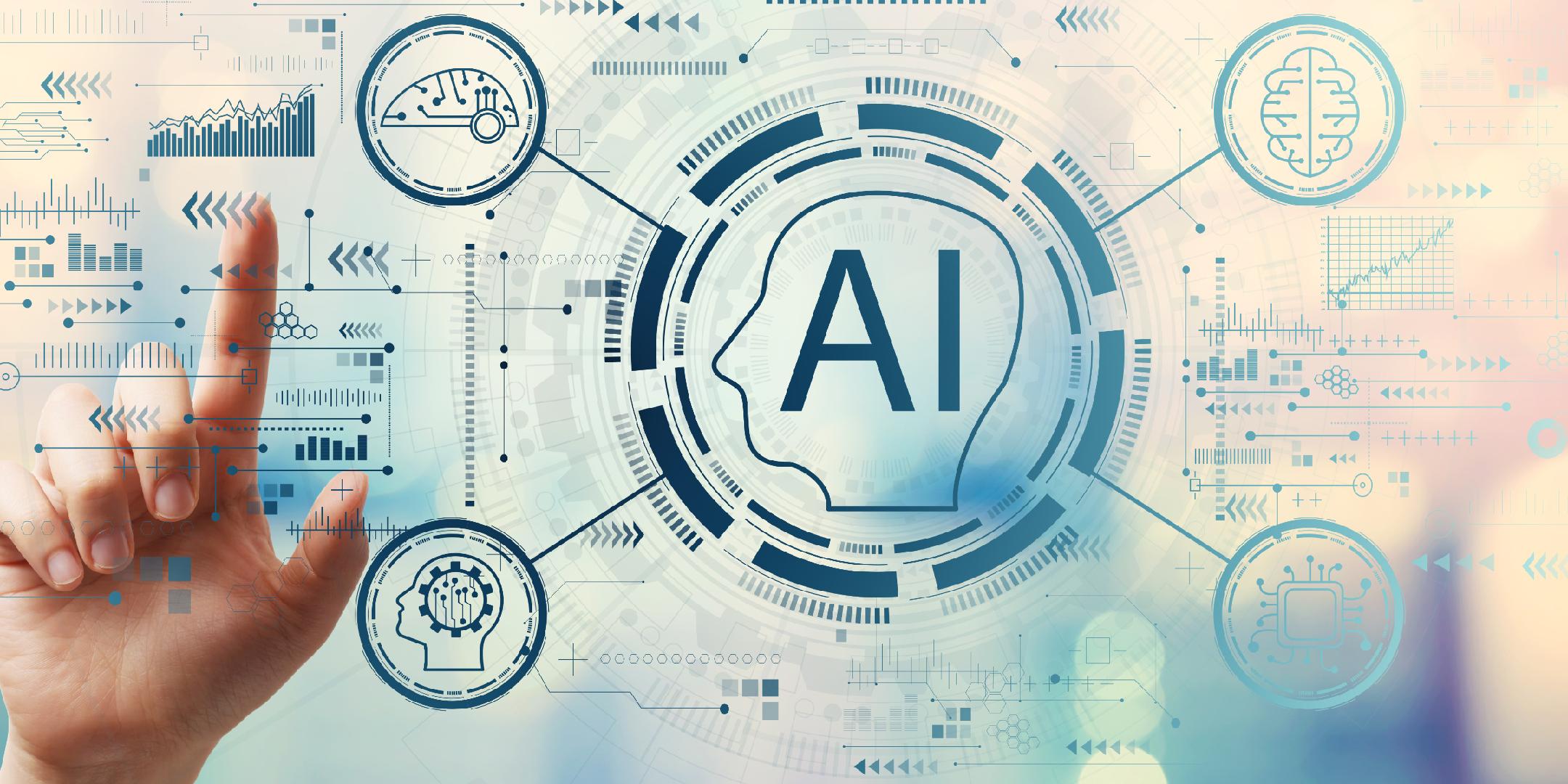
劉誠/文
歷史上,全球大國的崛起總是與科技革命緊密相連。
當(dāng)今時(shí)代,全球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恰逢新一輪科技革命的到來,AI領(lǐng)域的國際競爭也愈演愈烈。從歷史、經(jīng)濟(jì)和政治的視角分析科技革命,并預(yù)判AI國際競爭態(tài)勢(shì),這值得社會(huì)各界密切關(guān)注。
歷史邏輯:科技中心的演變
1954年,英國學(xué)者約翰·德斯蒙德·貝爾納(John Desmond Bernal)在其著作《歷史上的科學(xué)》中,首次系統(tǒng)地提出了“全球科學(xué)中心轉(zhuǎn)移”這一學(xué)術(shù)命題,探究了全球科學(xué)活動(dòng)主導(dǎo)地位在地理空間層面上的歷史性變遷情況。
1962年,日本科學(xué)史家湯淺光朝通過定量統(tǒng)計(jì)分析發(fā)現(xiàn),近代以來,全球科學(xué)中心按照“意大利—英國—法國—德國—美國”的順序依次轉(zhuǎn)移,轉(zhuǎn)移周期大約為80年,這一規(guī)律被后世稱作“湯淺現(xiàn)象”周期律。
美國耶魯大學(xué)歷史學(xué)教授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在1992年曾經(jīng)指出,從歷史上看任何大國的崛起都與科技創(chuàng)新緊密相連,都遵循著“科技創(chuàng)新—國內(nèi)標(biāo)準(zhǔn)國際化—提供區(qū)域和國際公共產(chǎn)品—主導(dǎo)國際輿論”的成長路徑。
也就是說,科技中心是經(jīng)濟(jì)中心、政治中心、文化教育中心以及軍事中心的先導(dǎo)力量,是大國崛起的第一步。
經(jīng)濟(jì)邏輯:經(jīng)濟(jì)范式的躍遷
然而,科技革命并不必然引發(fā)產(chǎn)業(yè)革命。例如,各大文明古國雖有許多偉大的科技發(fā)明,卻未能催生出現(xiàn)代工業(yè);意大利作為近代第一個(gè)全球科技中心,也未能率先掀起產(chǎn)業(yè)革命。
這說明,我們不能簡單地將科技革命等同于產(chǎn)業(yè)革命,二者之間存在一定“鴻溝”。換句話說,科技革命需要實(shí)現(xiàn)“驚險(xiǎn)一躍”,即通過商業(yè)化、產(chǎn)業(yè)化、規(guī)模化生產(chǎn),才能轉(zhuǎn)化為產(chǎn)業(yè)革命,這實(shí)際上需要形成系統(tǒng)性的經(jīng)濟(jì)范式轉(zhuǎn)換。
正如美國科學(xué)哲學(xué)家托馬斯·庫恩(Thomas Samuel Kuhn)在《科學(xué)革命的結(jié)構(gòu)》一書中所指出的:“科學(xué)的發(fā)展不是通過連續(xù)和線性的方式,而是經(jīng)歷一系列‘范式轉(zhuǎn)換’來發(fā)展的。”具體而言,這需要一套從技術(shù)到經(jīng)濟(jì)的完整范式,涵蓋生產(chǎn)設(shè)備、燃料能源動(dòng)力、基礎(chǔ)設(shè)施、城鎮(zhèn)化、人口結(jié)構(gòu)、市場規(guī)模,以及適應(yīng)新產(chǎn)業(yè)發(fā)展的社會(huì)規(guī)則等多個(gè)方面。
縱觀全球大國的科技史與經(jīng)濟(jì)發(fā)展史,通用技術(shù)(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GPT)在全社會(huì)的普及應(yīng)用,是實(shí)現(xiàn)經(jīng)濟(jì)范式轉(zhuǎn)換、完成從科技革命到產(chǎn)業(yè)革命“驚險(xiǎn)一躍”的關(guān)鍵所在。例如,蒸汽機(jī)啟動(dòng)了第一次產(chǎn)業(yè)革命,內(nèi)燃機(jī)和電氣化技術(shù)成為第二次產(chǎn)業(yè)革命的標(biāo)志,計(jì)算機(jī)和互聯(lián)網(wǎng)則引領(lǐng)了第三次產(chǎn)業(yè)革命。
也就是說,盡管科技革命中全社會(huì)涌現(xiàn)出大量發(fā)明創(chuàng)造,技術(shù)路線紛繁復(fù)雜,但從技術(shù)經(jīng)濟(jì)范式轉(zhuǎn)換的歷程來看,關(guān)鍵在于抓住其中的GPT技術(shù),并盡快實(shí)現(xiàn)經(jīng)濟(jì)范式轉(zhuǎn)換,從而引領(lǐng)全社會(huì)經(jīng)濟(jì)實(shí)現(xiàn)躍遷。
GPT作為一個(gè)明確的經(jīng)濟(jì)學(xué)概念,由斯坦福大學(xué)的蒂莫西·F·布雷斯納漢(Timothy F. Bresnahan)和特拉維夫大學(xué)的曼努埃爾·特拉伊滕貝格(Manuel Trajtenberg)于1992年首次提出。
在他們看來,技術(shù)具有一種樹狀結(jié)構(gòu),幾個(gè)主要技術(shù)位于頂端,其他所有技術(shù)均由它們派生而來。他們定義GPT具有三個(gè)重要特征:普遍適用性、創(chuàng)新互補(bǔ)性以及技術(shù)動(dòng)力性。鑒于GPT的重要意義,經(jīng)濟(jì)學(xué)家普遍認(rèn)為,GPT在國家經(jīng)濟(jì)崛起過程中發(fā)揮著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
政治邏輯:大國的崛起
經(jīng)濟(jì)基礎(chǔ)決定上層建筑,科技和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必然會(huì)導(dǎo)致國際權(quán)力的集中,進(jìn)而引發(fā)大國的崛起。對(duì)此,存在兩種不同的理論解釋。
第一種解釋是新范式的中心崛起與外圍擴(kuò)散。
可以說,科技革命引發(fā)的產(chǎn)業(yè)革命,天然地推動(dòng)了世界權(quán)力中心的轉(zhuǎn)移。尤其是,GPT帶來了科技革命以及大國崛起的可能性。
經(jīng)濟(jì)學(xué)家關(guān)注一個(gè)國家如何借助GPT出現(xiàn)所帶來的社會(huì)經(jīng)濟(jì)范式轉(zhuǎn)換以及國際產(chǎn)業(yè)和權(quán)力中心的轉(zhuǎn)換機(jī)遇,從而推動(dòng)大國崛起。
有學(xué)者強(qiáng)調(diào)全球基礎(chǔ)設(shè)施的重要性,因?yàn)橐粋€(gè)大國若要抓住科技變革的機(jī)遇,就需要在GPT發(fā)展初期積極建設(shè)與之相關(guān)的基礎(chǔ)設(shè)施。
在這個(gè)過程中,不僅有技術(shù)革命,更有基礎(chǔ)設(shè)施、經(jīng)濟(jì)發(fā)展范式等方面的全面轉(zhuǎn)型與變革。比如,航海和港口的發(fā)展,曾為英國、荷蘭、西班牙等國家的崛起提供了機(jī)遇;鐵路和電報(bào)電信曾為美國的崛起提供了機(jī)遇;高鐵、汽車、電子元器件、互聯(lián)網(wǎng)為二戰(zhàn)后日本及亞洲四小龍的騰飛提供了機(jī)遇。
權(quán)力中心在塑造大國的同時(shí),也會(huì)同步形成一些圍繞大國的小國,進(jìn)而形成中心外圍權(quán)力秩序。
有學(xué)者深入探討了技術(shù)擴(kuò)散和大規(guī)模應(yīng)用對(duì)于大國秩序演變的作用,提出了GPT擴(kuò)散理論,并指出決定哪個(gè)國家能夠擁抱未來的關(guān)鍵在于GPT的基礎(chǔ)設(shè)施,而不僅僅是在創(chuàng)新領(lǐng)域搶占高地。
與新的GPT相適應(yīng)的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需要形成產(chǎn)業(yè)革命與金融資本相融合的新范式。在這一過程中,新范式要突破舊有社會(huì)制度框架的阻礙,在舊有體系斷裂時(shí)吸收技術(shù)革命的新范式,并與新形成的社會(huì)制度框架重新耦合,從而發(fā)揮GPT的技術(shù)互補(bǔ)性,使其在大國崛起中發(fā)揮更大作用。
從中也可以看出,中心外圍的國際權(quán)力格局在一定時(shí)期內(nèi)是相對(duì)穩(wěn)定的,中心國家在實(shí)現(xiàn)利益最大化的同時(shí),外圍國家能獲得技術(shù)溢出和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的好處,彼此相互成就、共同成長。
正如美國著名的國際關(guān)系和國際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家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于2006年所指出的,科技革命和產(chǎn)業(yè)變革是核心區(qū)經(jīng)濟(jì)快速增長以及相對(duì)其他社會(huì)興起的主要原因,隨后新技術(shù)和產(chǎn)業(yè)就會(huì)擴(kuò)散到邊緣區(qū)經(jīng)濟(jì)體。
吉爾平還提出,隨著崛起大國的經(jīng)濟(jì)增長率因革新速度變得相對(duì)有限而呈低速態(tài)勢(shì),其經(jīng)濟(jì)、技術(shù)和組織技能的擴(kuò)散會(huì)削弱它對(duì)其他國家,尤其是那些處于體系外圍的國家的競爭優(yōu)勢(shì),此時(shí)新興國家獲得后發(fā)優(yōu)勢(shì),這推動(dòng)了國際權(quán)力體系的進(jìn)一步更迭。
第二種解釋是技術(shù)主權(quán)和技術(shù)民族主義。
一方面,依賴與被依賴構(gòu)成權(quán)力。在國際政治理論中,權(quán)力工具是指國家在國際體系中捍衛(wèi)其自主權(quán)和施加影響力的手段,包括經(jīng)濟(jì)實(shí)力、軍事實(shí)力、軟實(shí)力以及對(duì)通信的控制。
從經(jīng)濟(jì)學(xué)角度看,經(jīng)濟(jì)上的相互依賴可以被用作競爭的權(quán)力工具。由于經(jīng)濟(jì)上的相互依賴很少是對(duì)稱的,各國努力發(fā)展非對(duì)稱性相互依賴,以最大限度地發(fā)揮其自主權(quán)和影響力。
例如,中國于2013年發(fā)起共建“一帶一路”以及“數(shù)字絲綢之路”,這表明中國正在削弱美國對(duì)作為地緣經(jīng)濟(jì)力量重要支柱的海上運(yùn)輸走廊的控制。
另一方面,對(duì)他國技術(shù)的依賴會(huì)損害本國主權(quán)。倘若關(guān)鍵技術(shù)受制于人,就會(huì)對(duì)他國形成非對(duì)稱性依賴,影響本國在經(jīng)濟(jì)、政治、軍事、外交等方面國際戰(zhàn)略的自主性。
技術(shù)不自主,其他方面也難以自主。例如,由于不是技術(shù)領(lǐng)導(dǎo)者,俄羅斯幾乎沒有能力與美國和中國的技術(shù)生態(tài)系統(tǒng)相抗衡。非洲一些國家面臨的一個(gè)國際威脅是,在技術(shù)積累和實(shí)施方面過于落后,從而因過度依賴外國企業(yè)而成為“技術(shù)殖民地”,這會(huì)使其市場飽和并阻礙國內(nèi)替代品走向成熟。解決這一問題的最佳方法是通過與中國合作,建立本地技術(shù)儲(chǔ)備,并將本地產(chǎn)業(yè)發(fā)展納入全球技術(shù)生態(tài)系統(tǒng)中。
時(shí)代邏輯:AI國際競爭
首先,怎么看這個(gè)時(shí)代?
當(dāng)前,全球呈現(xiàn)出多元科技中心、多元經(jīng)濟(jì)中心的格局,競爭態(tài)勢(shì)愈發(fā)復(fù)雜。
歷史上存在一個(gè)看似矛盾的現(xiàn)象:一國獨(dú)大與全球自由秩序并存。當(dāng)一國在科技革命中迅速崛起,且其他國家尚不構(gòu)成威脅時(shí),國際分工會(huì)鞏固該國對(duì)戰(zhàn)略產(chǎn)業(yè)、運(yùn)輸走廊和金融工具等地緣經(jīng)濟(jì)權(quán)力杠桿的控制,使其能夠通過全球化放大技術(shù)優(yōu)勢(shì)所帶來的市場紅利。
因此,該大國會(huì)主張全球化,并愿意分享其先進(jìn)技術(shù)。與此同時(shí),具備技術(shù)基礎(chǔ)的追隨者通過模仿和學(xué)習(xí)逐漸成為新興國家,它們有很強(qiáng)的動(dòng)力推動(dòng)技術(shù)更快地?cái)U(kuò)散,進(jìn)而形成了相對(duì)穩(wěn)定的自由經(jīng)濟(jì)國際秩序。
反之,當(dāng)經(jīng)濟(jì)權(quán)力的集中度降低時(shí),自由秩序預(yù)計(jì)將瓦解,相關(guān)政權(quán)會(huì)變得更為脆弱,最終可能被重商主義安排所取代,此時(shí)國家權(quán)力將建立在市場力量之上。
第四次產(chǎn)業(yè)革命就發(fā)生在這樣一個(gè)支離破碎的國際經(jīng)濟(jì)體系中。美歐日等經(jīng)濟(jì)體對(duì)自由貿(mào)易的承諾減少,這一重大變化將使它們的經(jīng)濟(jì)戰(zhàn)略變得更加肆無忌憚、更具強(qiáng)制性和破壞性。
其次,怎么看AI?
當(dāng)今社會(huì)已從平臺(tái)經(jīng)濟(jì)時(shí)代邁入智能經(jīng)濟(jì)時(shí)代,從數(shù)字化階段進(jìn)入智能化階段。從中日對(duì)比來看,日本實(shí)際上抓住了第三次產(chǎn)業(yè)革命的機(jī)遇,但在個(gè)人電腦、智能手機(jī)和平臺(tái)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過程中錯(cuò)失良機(jī)。中國抓住了第四次產(chǎn)業(yè)革命在個(gè)人電腦、智能手機(jī)、平臺(tái)經(jīng)濟(jì)、新能源汽車、自動(dòng)駕駛等方面的機(jī)遇,但在第三次產(chǎn)業(yè)革命中存在歷史遺留的短板(如芯片半導(dǎo)體領(lǐng)域)。
我們亟待研究的是:與第三次產(chǎn)業(yè)革命相比,第四次產(chǎn)業(yè)革命新在何處?從日本在第三次產(chǎn)業(yè)革命中的表現(xiàn)中能汲取哪些經(jīng)驗(yàn)和教訓(xùn)?例如,如何更快更穩(wěn)地抓住AI機(jī)遇,實(shí)現(xiàn)人機(jī)協(xié)作、虛實(shí)融合、實(shí)智融合發(fā)展。
其三,我們?nèi)绾卧谶@個(gè)時(shí)代搶占AI國際競爭優(yōu)勢(shì)?
新一輪科技革命呈現(xiàn)出科技革命與產(chǎn)業(yè)革命深度融合的顯著特征,其核心在于以新興科技為驅(qū)動(dòng)力,推動(dòng)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的根本性變革和生產(chǎn)力的跨越式提升。
首先,新技術(shù)的集群化突破形成了新的生產(chǎn)力體系。人工智能、大數(shù)據(jù)、量子計(jì)算及清潔能源技術(shù)等新興領(lǐng)域的突破,正在重塑傳統(tǒng)產(chǎn)業(yè)的生產(chǎn)模式,并催生出智能制造、綠色能源及數(shù)字經(jīng)濟(jì)等新興業(yè)態(tài)。
其次,產(chǎn)業(yè)生態(tài)的塑造成為經(jīng)濟(jì)競爭的關(guān)鍵。與以往的單點(diǎn)技術(shù)突破不同,本輪科技革命強(qiáng)調(diào)技術(shù)系統(tǒng)間的協(xié)同發(fā)展,促成了上下游產(chǎn)業(yè)鏈的生態(tài)化重構(gòu)。以新能源汽車產(chǎn)業(yè)為例,智能化與電動(dòng)化的深度融合,不僅革新了汽車制造的傳統(tǒng)模式,更深刻重塑了能源供應(yīng)、材料科學(xué)及軟件開發(fā)等領(lǐng)域的協(xié)同生態(tài)。
最后,產(chǎn)業(yè)部門成為技術(shù)創(chuàng)新的重要力量。以人工智能大模型為例,隨著大模型成為引領(lǐng)本輪人工智能革命的技術(shù)范式,擁有更多數(shù)據(jù)和算力資源的產(chǎn)業(yè)界逐漸超越學(xué)術(shù)界,成為推動(dòng)人工智能發(fā)展的主角。

 京公網(wǎng)安備 11010802028547號(hào)
京公網(wǎng)安備 11010802028547號(hà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