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jīng)濟觀察報 關(guān)注
2025-09-06 01:2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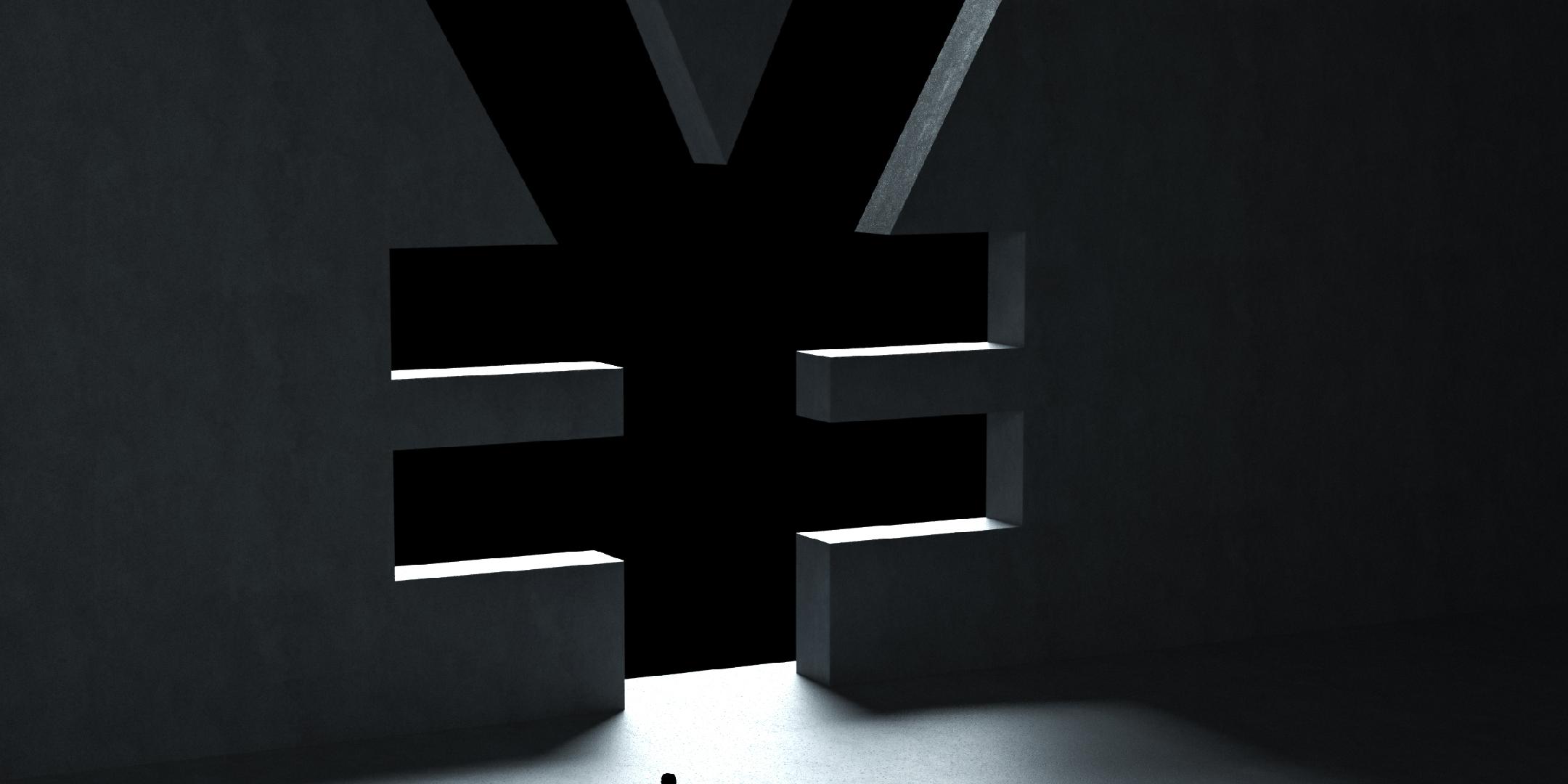
繆因知/文
今年,我國出現(xiàn)了兩起具有標志性意義的“首案”——上市公司內(nèi)部人因違反增持承諾和不減持承諾,被法院判決賠償數(shù)百萬元。這兩起案件為上市公司董事、監(jiān)事、高管、5%以上大股東及其一致行動人等敲響了“承諾不可輕做、不可輕違”的警鐘。
這兩個首案處于虛假陳述賠償責任的前沿領(lǐng)域,其反映的追責趨勢是否會進一步擴張,又是否應(yīng)有合理限制,值得深入分析。需要說明的是,本人與文中提及的任何公司、個人及其親友、員工、代理人均無往來。
增持承諾不兌現(xiàn):視同虛假陳述
2021年6月15日,上海金力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發(fā)布公告,稱董事兼總裁袁某、控股子公司總經(jīng)理羅某計劃在6個月內(nèi)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額合計不低于3億元。此后,金力泰兩次公告稱,袁某、羅某的上述增持承諾履行期限分別延期至2022年6月15日、9月30日。2022年9月30日,金力泰公告稱袁某、羅某未能在延期期間完成增持計劃。同年10月20日,證監(jiān)會上海監(jiān)管局對袁某、羅某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監(jiān)管措施。同年12月21日,深圳證券交易所作出《關(guān)于對袁某、羅某給予公開譴責處分的決定》。
2024年5月,上海金融法院將本案作為首例因上市公司董監(jiān)高未履行公開增持承諾引發(fā)的證券侵權(quán)糾紛案件予以受理。原告劉某某、鄭某某主張,他們因上述股份增持承諾購買了金力泰股票,該行為構(gòu)成證券虛假陳述,要求金力泰、袁某、羅某共同賠償投資差額損失、傭金損失等共計900余萬元。
被告辯稱,他們已按照規(guī)定及時將增持意愿、資金籌措情況以及因資金籌措困難導(dǎo)致延期等情況書面告知金力泰,因客觀上履行能力不足,無法再履行增持承諾,不存在主觀上“忽悠式增持”的故意或過失。對此,公司也及時發(fā)布了公告。股價下跌主要是由于市場整體及企業(yè)自身經(jīng)營等其他情況導(dǎo)致,并非兩被告不履行增持承諾所致。
2025年4月,上海金融法院經(jīng)審理認為:公開承諾涵蓋股份限售承諾、業(yè)績承諾、股份增(減)持承諾、分紅承諾、股份回購承諾、法定義務(wù)重述承諾等多種類型。不履行公開承諾的法律責任屬性無法一以概之,應(yīng)結(jié)合承諾主體及內(nèi)容、相對人是否確定、未履行承諾的原因、承諾主體的過錯等因素綜合考量,可能構(gòu)成虛假陳述、操縱市場等典型證券侵權(quán)行為,也可能無法歸入證券特殊侵權(quán)范疇,抑或構(gòu)成違約行為。
對具體行為應(yīng)結(jié)合增持行為特點、承諾的行為性質(zhì)、承諾時的履約準備、延期事由、未履行承諾原因等綜合判斷。袁某、羅某在首次作出增持承諾時并無資金準備,在后續(xù)延期過程中也未積極籌措資金,且在面對交易所質(zhì)詢時,以過橋資金制作“虛假”存款證明,故難以認定其有增持的真實意愿。從增持主體、承諾增持金額、市場影響力等角度看,這一公開增持承諾信息的披露,對證券市場和投資者預(yù)期產(chǎn)生了嚴重誤導(dǎo),虛假陳述行為成立且具有重大性。換言之,法院認為這兩位高管并非真心準備增持,增持未兌現(xiàn)是主觀而非客觀因素所致。
至于公司,法院認為其盡到了基本的審查義務(wù),亦無證據(jù)證明其明知或應(yīng)知袁某、羅某存在虛假陳述,故不應(yīng)就此承擔民事賠償責任。
綜上,經(jīng)委托第三方機構(gòu)進行損失核定,一審判令被告袁某、羅某共同賠償兩原告投資損失 506130.96元、277406.42元。而且,由于本案采用示范判決機制進行審理,后續(xù)還會有不少其他原告提起的同類判決會參照此判決結(jié)果。
本案在責任定性層面爭議較小。在定量層面,兩人實際增持0股,屬于100%未履行承諾,不存在減輕責任的理由。法院將不履行增持承諾視為制造了一個虛假的利好信息。承諾到期未履行后,本案又屬于股價下跌的典型場景。所以,法院在利好信息破滅時,要求承諾人賠償投資者“買高賣低”導(dǎo)致的損失,邏輯較為通順。后續(xù)出現(xiàn)其他案件同類判決的概率較大。
不減持承諾被違反:可以進行場景三分法嗎?
需要注意的是,金力泰案判決的法律依據(jù)是新證券法新增的第84條第2款。該條款行文較為寬泛,其內(nèi)容為“發(fā)行人及其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董事、監(jiān)事、高級管理人員等作出公開承諾的,應(yīng)當披露。不履行承諾給投資者造成損失的,應(yīng)當依法承擔賠償責任”。
由此可見,任何承諾未來都有可能招致賠償責任或賠償訴訟的風(fēng)險,比如控制人、董監(jiān)高承諾完成某項并購重組,甚至承諾守法合規(guī)。
和增持股票承諾最接近的,當屬不減持的承諾。從法律構(gòu)造上而言,承諾增持但未履行,和承諾不減持但未履行,本質(zhì)是一樣的。股票和一切商品的基本規(guī)律是供求影響價格。有人承諾增持,股價就有向上的動能;有人承諾不減持,股價就有維持的力量。除了資金因素外,董監(jiān)高、實控人等內(nèi)部人的承諾,也會給外部投資者帶來一定的信心。一旦打破承諾,股價就會下跌,這與吹噓公司利潤有1億元,但后來被揭穿的情況類似。
此前,對于違諾減持的行為,一般追究行政責任。相關(guān)行政罰款雖然金額不菲,但與民事賠償是不同的概念。目前尚無投資者提起賠償訴訟的案例。不過,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由于公司和股東之間的特殊約定,而判令違背不減持承諾的股東賠償?shù)陌咐?/p>
2025年7月發(fā)布的南方某省證券虛假陳述侵權(quán)案件審判白皮書中,第一則案例就涉及減持承諾的賠償判決。法院稱之為“上市公司訴股東違反限售承諾民事責任第一案”,甚至認為該案“對內(nèi)幕交易、操縱股價等證券違法行為非法收益的認定均具有參考意義”。
該案中,禾某公司于2017年上市時,公司實控人的一致行動人、董事夏某在招股書中承諾:上市36個月后的兩年內(nèi)(即第四、第五年),每年減持股份數(shù)量不超過所持上市前股份數(shù)量的15%;如違反承諾提前減持股份,應(yīng)向投資者道歉、回購?fù)葦?shù)量股份,并將減持收益返還給公司等。
2019年8月,夏某和妻子丁文某離婚,夏某將630萬股股份轉(zhuǎn)給丁某。一般來說,限售股份由于離婚、繼承而轉(zhuǎn)歸他人,未必一定會伴隨限售義務(wù)的轉(zhuǎn)變。但本案中,丁文某出具承諾函,確認繼續(xù)遵守夏某之前做出的限售承諾。2021年7月至11月,丁文某違反限售承諾提前減持股票,減持價款約5100萬元。2022年,該上市公司依據(jù)上述限售承諾函訴至法院,要求丁某向公司返還違規(guī)減持股份價款。
法院審理認為:上市公司股東、董監(jiān)高自愿作出的限售承諾屬于單方民事法律行為,自成立時即具有法律約束力,非依法律規(guī)定或未經(jīng)對方同意,不得擅自變更或解除。雖然法律未必明確要求違規(guī)減持需承擔何種具體責任,但違規(guī)減持行為本身具有不當性,應(yīng)當承擔相應(yīng)的法律責任。股東承諾違規(guī)減持收益歸公司,上市公司據(jù)此要求該股東支付違規(guī)減持收益的,應(yīng)予支持。
值得疑問的是,應(yīng)當向公司返還的違規(guī)減持的股款如何計算。法院認為:違規(guī)減持股票收益的計算方法并不唯一,應(yīng)根據(jù)個案具體情況確定。違規(guī)減持行為發(fā)生后,上市公司的股價可能出現(xiàn)三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是股價下跌。此時,違規(guī)減持收益的計算方式可以是“違規(guī)減持所得”和“合規(guī)減持應(yīng)得”之間的差額。比如,股東在股價10元時高位減持,限售期滿時的股價為8元,那么違規(guī)減持收益就是2元。
第二種情況是股價上漲。比如,股東在股價10元時高位減持,限售期滿時的股價為12元。從結(jié)果看,股東提前賣出是吃虧了。不過,有些公司給股東的承諾模版里會寫:如果違反不減持承諾,就在若干個交易日內(nèi)回購違規(guī)賣出的股票,且自回購?fù)瓿芍掌饘⑺秩抗煞莸逆i定期自動延長若干個月等。
法院認為可以參照限售承諾人在回購義務(wù)產(chǎn)生之日應(yīng)付出的回購成本和其違規(guī)出售股票價款之間的差額確定違規(guī)減持收益,該差額是限售承諾人得以避免的一項支出,可以作為確定其收益的參考依據(jù)。比如,減持后股價在10個交易日內(nèi)漲到11元,股東違規(guī)減持后本應(yīng)承諾在10個交易日內(nèi)贖回,但堅持不回購,就產(chǎn)生了每股1元的違法收益。
本案即是如此。2020年7月28日為限售起始日,交易均價為7.76元/股;2021年7月28日為被告股東減持起始日,交易均價為18.64元/股;2021年9月18日公司發(fā)布的《關(guān)于股東違反承諾減持公司股份的公告》,指出丁文某違諾減持;2021年11月18日減持終了日,交易均價為39.18元/股;2022年7月27日(限售期滿日),交易均價為37.64元/股。
2021年7月28日至2021年11月 18日期間,丁文某累計減持3065200股,減持所得金額75744958元,均價24.71元/股;其中合規(guī)減持即本來就能減持的股票為945000股,所得金額24323870元,均價25.74元/股;超過合規(guī)比例之外的減持股票數(shù)量為2120200股,所得金額51421088元,均價24.25元/股。
一審法院認為丁文某應(yīng)該在公司公告指出其違諾減持之日(2021年9月18日)起,按照此前10個交易日內(nèi)回購的承諾,不遲于第10個交易日(2021年10月12日)的交易均價為基準,計算出其所得收益為6926365.51元〔(超比例減持年度所得股票額75744958元÷賣出股數(shù)3065200股—2021年10月12日成交額91840000元÷2021年 10月 12日成交量4282700股)×超比例股數(shù)2120200股〕歸公司所有。
二審法院認為,一審判決未將丁文某合規(guī)減持的股票數(shù)量和所得款予以剔除,所以按照違規(guī)減持所得51421088元減去回購義務(wù)產(chǎn)生日(2021年10月12日)丁文菁應(yīng)付回購價款45457088元(該日股票成交均價21.44元/股×違規(guī)減持股數(shù)2120200股)計算,酌定違反限售承諾的收益為596.4萬元。根據(jù)限售承諾,其應(yīng)向公司返還該筆收益。
第三種情況是違規(guī)減持價格和后續(xù)股價持平。法院認為,此種情況下可以參考違規(guī)減持價款的資金占用費確定違規(guī)減持收益。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種算法的邏輯并非完全一致。第一種股價下跌的情況指向股東“偷跑”的違法收益,相對容易理解。
第二種股價上漲的情況中,違規(guī)違諾減持股東并無明顯法定的回購義務(wù)。如果不曾承諾回購,就不能采用這種計算方法。如果說同樣是違規(guī)違諾減持,有承諾回購的股東有違法收益,未承諾回購的股東無違法收益,這似乎也不通。
而且,股東承諾不減持和回購在前,減持行為發(fā)生在后,承諾甚至減持時當然無法預(yù)判未來股價。如果在股價上漲情形中原告和法官拿回購說事,那么在下跌情形中,做過回購承諾的股東是否也能主張按照“回購義務(wù)產(chǎn)生之日應(yīng)付出的回購成本”計算呢?
甚至,如果股東在股價下跌后的確回購了股票、補足了原來的持股量并承諾繼續(xù)鎖定,難道就不能“洗白”了嗎?比如,股東在股價10元時減持,限售期滿時的股價為8元,違規(guī)減持收益是2元。后來又于限售期滿或未滿時的9元價位時回購補足數(shù)量,能否主張實際違法收益最多是1元?
第三種股價持平的情形其實和股價上漲的情形一樣,未必不能說違規(guī)違諾減持并未產(chǎn)生對股價的不當壓力。就算這是違法行為,也不一定有重大性作用力和對他人的實際損害。
坦率地說,本人不太理解“違規(guī)減持價款的資金占用費”標準。新老股東都是用自有資金買股票,沒有占用公司資金。違規(guī)違諾減持所得的股價款也不是來自公司,而是來自其他投資者即接手這些股票的買主。如果沒有這筆減持,那筆資金當然還在其他投資者手里。但現(xiàn)在有了減持交易,原股東賣股得錢,就算提前占用了新股東的資金嗎?
的確,股價不漲不跌,新股東買了個寂寞,這筆投資不算很成功。但說違規(guī)減持的股東占用了新股東的資金,這算是一種有新意的說法。一分錢沒出過的公司去收取這筆“資金占用費”的理由又是什么呢?好在證券公開市場交易是匿名化的,沒人知道違規(guī)違諾減持股東的接盤俠是誰。如果違規(guī)違諾減持是通過大宗交易之類給特定人的,該新股東回頭起訴公司要求拿那筆“資金占用費”,法官又該如何回應(yīng)?
更宏觀的一個問題是:法律規(guī)則應(yīng)當有一致性的邏輯,而上述三種計算方法的邏輯有待統(tǒng)一。為什么股價持平才考慮資金占用費,股價下跌或上漲就不考慮了?為什么股價上漲和持平時不考慮回購義務(wù)標準?
三種情況三種算法,給人一種未必正確的感覺,似乎就是為了尋找收益而尋找收益,總之一定要找出某種收益以便判令賠償,而不是依據(jù)一種客觀平實的計算方法,不帶預(yù)判地去計算有沒有收益、有沒有損害。這個思路一旦打開,違諾不增持的案例也會變得更復(fù)雜。
增減持賠償責任應(yīng)有合理限制
近年來,虛假陳述賠償責任的范圍不斷擴張,法院對于在各種新型案例情形下確立首案也頗有積極性。但無論如何,審判都應(yīng)當遵守法理法律,并注意利益的平衡。
法院接受新型案件,有利于更好地解決社會糾紛。但案情是特定化的,法律是中立的,并非每一個場景的首案都必須給出有責結(jié)論,才是值得一提的首案。依法指出特定情形下無責,同樣是一個有益的首案。法院必須依照法律判案。如果法律本身規(guī)定得不夠周全,哪怕存在漏洞,法院也不一定要堅持按自己的想法去在個案中“懲治壞人”。否則,以后遇到近似案例時,就不一定能自圓其說。
違諾不增持或減持是近年才出現(xiàn)的邊緣性、新型證券違法案型,其危害程度未必比得上財務(wù)造假等傳統(tǒng)硬核的虛假陳述情形,對此應(yīng)慎重處理。
首先,應(yīng)當合理看待具體增減持行為的作用力。違背承諾自然是不對的,違背承諾的行為者一般也會承擔來自監(jiān)管者的行政責任,并非可以輕松避責。但民事侵權(quán)責任依法需要以因果關(guān)系、過錯等因素為基礎(chǔ),也應(yīng)當考察相關(guān)行為本身有無重大性。
中國的虛假陳述賠償制度本身適用了大量推定,如推定虛假陳述行為對投資者決策造成了影響,推定對投資者造成了損失,故而在適用時應(yīng)當有合理限制。小股東(如持股1%以下者)違背諾言不增持或減持的行為,或者相對于公司市值案涉金額不大的行為,或者承諾未完成比例較低(如低于10%)的承諾,本身對市場交易和其他投資者決策不會有大的負面影響。當事人因為客觀原因(如破產(chǎn)、失業(yè)等)而非因主觀過錯而不能履行承諾的,也可予以免責。
其次,對于違反承諾案件,應(yīng)當優(yōu)先允許當事人以繼續(xù)履行承諾的方式來糾正行為的影響。財務(wù)造假之類的傳統(tǒng)虛假陳述做出后,當事人無法通過改口來完全消除影響。但增持減持和其他很多類型的承諾未必不能通過補充履行、矯正履行(如回購),特別是及時實施此類履行來彌補,此時對相關(guān)行為可以不再追究賠償責任,除非投資者能起訴證明延遲履行承諾本身造成了一部分獨立的、不可彌補的損害。
事實上,違規(guī)違諾不增持或減持的行為本身存在著實際作用力,對股價的影響機制不同于傳統(tǒng)虛假陳述。比如對于虛報利潤,可以推定后來的股價下跌源于此等不實信息被揭露的作用力。但說增持卻又不增持,股價下跌的部分原因是由于無資金托舉,而不能全部怪罪于此前陳述的信息不實。
證券價格說到底是取決于其價值基本面,不能只靠內(nèi)部股東的托舉。如果基本面不行,僅靠內(nèi)部股東增持或不減持,反而會制造虛假繁榮和未來股價進一步崩盤的風(fēng)險。只是由于我國的董監(jiān)高和內(nèi)部股東股份限售制度異常嚴格,獨冠全球,所以內(nèi)部股東的增減持仿佛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制度,甚至被一些人視為“基礎(chǔ)性制度”。此中的法律問題辨析較為復(fù)雜,限于篇幅,暫不展開。

 京公網(wǎng)安備 11010802028547號
京公網(wǎng)安備 11010802028547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