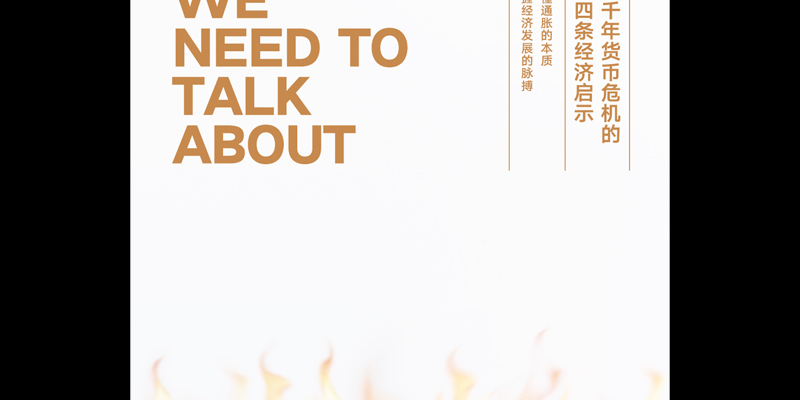
“通貨膨脹無處不在,并且總是一種貨幣現(xiàn)象。”米爾頓·弗里德曼的這句名言,高度概括了貨幣主義者對于通脹的看法。然而,在現(xiàn)代經(jīng)濟(jì)體中,通脹的成因和內(nèi)在機(jī)制是多樣的,各國央行對通脹的判斷、態(tài)度和政策制定也存在差異。匯豐銀行首席經(jīng)濟(jì)學(xué)家簡世勛的新著《通脹的教訓(xùn)》,透視了兩千年來的貨幣危機(jī),分析了央行與政府在通脹形成及治理過程中的角色。特別是總結(jié)了通脹的“四項測試”準(zhǔn)則和十四條經(jīng)驗教訓(xùn),以作為央行和政策制定者的參考。
作為曾經(jīng)的中央銀行家,作者以史為鑒,總結(jié)了抗擊通脹的經(jīng)驗得失,為治理通脹提供借鑒。同時,作者也為重新審視通脹提供了更多元的視角。通過作者的觀察和分析可以發(fā)現(xiàn),當(dāng)代的通脹現(xiàn)象,既與傳統(tǒng)貨幣主義者的看法存在明顯差別,也與經(jīng)典宏觀理論的假定存在諸多矛盾之處。例如,現(xiàn)代貨幣理論的基石之一是主張央行獨立,認(rèn)為民選政府能夠獨立維護(hù)貨幣價值,央行的獨立性使其能夠避免受到選舉周期的誘惑,也不太容易為財政所輕易主導(dǎo)。然而,事實卻與此大相徑庭。
20世紀(jì)80年代的歷史經(jīng)驗表明,央行獨立遠(yuǎn)非看上去那么簡單。一方面,民主選舉產(chǎn)生的政府并不能完全抵擋通脹的誘惑,因為緊縮政策在政治上終究不能成為取悅選民的政策選擇。相反,對于政府和政治家而言,印鈔始終有著致命的吸引力——它既是增稅或減支的絕佳替代方式,又可以隱蔽地掠奪民眾儲蓄,還能避開緊縮政策所帶來的政治阻力與社會不滿。這也印證了貨幣主義者的名言——通脹是“與印刷機(jī)有聯(lián)系的現(xiàn)象”。
另一方面,作者還觀察到,雖然理論上央行獨立有助于貨幣政策擺脫政治時間表的束縛,但事實上,央行在面對真正艱難的政策抉擇時,尤其是當(dāng)消除金融體系中的過度通脹需付出重大代價時,仍需要尋求某種形式的政治支持與認(rèn)可。20世紀(jì)80年代初,英格蘭銀行成功抗擊通脹的重要基礎(chǔ),是時任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夫人的支持。通脹治理所伴隨的巨大代價,往往離不開政治支持,特別是通脹挑戰(zhàn)越嚴(yán)峻,解決方案就越有可能帶有顯著的政治色彩,客觀上也更需要政治干預(yù)。因此,如果說央行有能夠脫離政治光譜的時刻,那也只能存在于通脹率低且穩(wěn)定的少數(shù)時期。
回溯歷史,無論是封建君主為籌集戰(zhàn)爭經(jīng)費、滿足奢侈消費,還是現(xiàn)代政府為推動增長而放松財政紀(jì)律、削弱央行獨立性,貨幣超發(fā)都被視為通脹的源頭。也正如這本書的作者在其另一部著作《貨幣放水的盡頭:還有什么能拯救停滯的經(jīng)濟(jì)》中所闡述的觀點,央行過度放松貨幣供應(yīng),終將導(dǎo)致通脹之禍。但是,現(xiàn)代通脹是否都源于貨幣超發(fā)?或者,貨幣寬松是否必然導(dǎo)致通脹呢?這些在理論上原本看似確定的答案,在審視過去30多年世界宏觀經(jīng)濟(jì)實踐時,顯然已經(jīng)不是那么確定了。
當(dāng)代各國政府所面臨的經(jīng)濟(jì)現(xiàn)實錯綜復(fù)雜,傳統(tǒng)觀念中“貨幣政策負(fù)責(zé)抑制通脹,財政政策負(fù)責(zé)穩(wěn)定經(jīng)濟(jì)”的觀點,顯得過于教條,甚至是脫離現(xiàn)實。現(xiàn)代宏觀經(jīng)濟(jì)政策的多種組合可能性,使宏觀調(diào)控日趨復(fù)雜。財政部與央行作為兩大核心機(jī)構(gòu),都具有擔(dān)當(dāng)宏觀政策主角的能力。當(dāng)財政坐在駕駛席上,央行充當(dāng)副駕駛時,中央銀行家顯然難以獨自承擔(dān)債務(wù)膨脹和通脹失職之責(zé);而即使當(dāng)央行處于駕駛席時,如前所述,央行要實現(xiàn)完全獨立也面臨挑戰(zhàn)。更何況,央行需要兼顧多個政策目標(biāo),這可能導(dǎo)致其同時采取方向相反的政策——例如,對抗通脹的有力措施往往會削弱增長,或是導(dǎo)致更多失業(yè),這都會將央行置于政策困境之中,最終將由政治決策來確定政策方向。
在過去幾十年中,對通脹控制保持樂觀態(tài)度是幸運的。就如美聯(lián)儲前主席本·伯南克曾堅稱的:“我對未來持樂觀態(tài)度,因為我堅信貨幣政策制定者不會忘記20世紀(jì)70年代的教訓(xùn)。”在新冠疫情暴發(fā)前的30多年間,除個別國家出現(xiàn)局部、偶發(fā)的小幅通脹外,全球主要經(jīng)濟(jì)體的通脹幾乎都處于休眠期。特別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jī)發(fā)生后,主要發(fā)達(dá)經(jīng)濟(jì)體都經(jīng)歷了較長的貨幣寬松時期,持續(xù)大規(guī)模貨幣放水與極低利率環(huán)境并存,卻沒有出現(xiàn)明顯通脹,“低利率、低通脹、低增長”似乎成為世界經(jīng)濟(jì)的常態(tài)。此外,甚至在日本等一些長期遭受通貨緊縮之困的國家,通脹仿佛已經(jīng)消失,“安倍經(jīng)濟(jì)學(xué)”的本質(zhì)就是通脹經(jīng)濟(jì)學(xué)。匯豐銀行前首席經(jīng)濟(jì)學(xué)家羅杰·布特爾在其著作《通脹的終結(jié)》中甚至宣稱:“通脹已死。”
正因如此,在20世紀(jì)七八十年代曾經(jīng)讓政策制定者心生恐懼的通脹幽靈,如今似乎卻變成了對政策制定者充滿誘惑的天使。各國央行始終對通縮保持警惕,更愿意相信“日本式通縮”才是真正的風(fēng)險所在,而認(rèn)為通脹問題不足為慮。在新冠疫情發(fā)生初期,盡管通脹警示信號紅燈閃爍,但各國央行卻遲遲不愿加息,政策當(dāng)局普遍認(rèn)為通脹只是暫時性的,而且很快就會消失。學(xué)術(shù)界也更傾向于將其解釋為疫情封鎖造成的供應(yīng)鏈沖擊,以及俄烏沖突等地緣政治紛爭的外溢效應(yīng),特別是與制裁俄羅斯帶來的能源短缺與價格飆升有關(guān)。因此,政策制定者選擇繼續(xù)維持寬松貨幣政策,這也是政治壓力最小的選擇。
但是,通脹真的消失了嗎?事實上,雖然通脹長時間沉寂,但從未真正離去。正是中央銀行家和經(jīng)濟(jì)學(xué)家對通脹警示信號的漠視或淡化態(tài)度,以及政策制定者的猶豫和綏靖政策,最終讓通脹在2021年又卷土重來。主要發(fā)達(dá)經(jīng)濟(jì)體所經(jīng)歷的高通脹,既表明貨幣超發(fā)仍然是通脹的潛在推動力量,也表明在錯綜復(fù)雜的宏觀環(huán)境下,引發(fā)通脹的因素日益多元化。因此,央行及時、準(zhǔn)確地識別通脹信號,決策者果斷采取行動至關(guān)重要,盡管這可能面臨政治壓力和社會阻力。為此,《通脹的教訓(xùn)》提出了“四項測試”準(zhǔn)則來判斷通脹風(fēng)險,以期為央行行長和政策制定者有效管控通脹風(fēng)險提供指南。
當(dāng)下,由美國挑起的全球貿(mào)易戰(zhàn)震驚世界,其造成的貿(mào)易秩序混亂和規(guī)則破壞,既擾亂了全球生產(chǎn)分工和供應(yīng)鏈體系,也必將使國別間總供求出現(xiàn)重大錯位。一方面,逆差國將面臨總供給跟不上總需求的局面,進(jìn)而引發(fā)價格顯著上漲;另一方面,順差國則可能因短期內(nèi)出口顯著下滑,加劇內(nèi)部總需求不足的矛盾,面臨通縮壓力。這種復(fù)雜的總量與結(jié)構(gòu)性失衡,很可能將2008年以來持續(xù)寬松政策所累積的貨幣“柴薪”再次點燃。目前,貿(mào)易逆差國本就存在顯著的通脹壓力,貿(mào)易戰(zhàn)恰似火上澆油,而順差國的產(chǎn)能壓力也將難以緩解,無異于雪上加霜。以鄰為壑的貿(mào)易戰(zhàn),將使通脹與通縮并存的世界經(jīng)濟(jì)難以實現(xiàn)互補(bǔ)與雙贏,并將對各國居民生活造成顯著傷害,也抑制全球經(jīng)濟(jì)增長。
以有效抗擊通脹而聞名的美聯(lián)儲前主席保羅·沃爾克曾犀利地指出,隨著經(jīng)濟(jì)現(xiàn)實的改變,政治環(huán)境也在發(fā)生變化,就連貨幣主義者都不再認(rèn)為“通脹最終是一種貨幣現(xiàn)象”,這在現(xiàn)代政治體系中正引起日益廣泛的共鳴。直面當(dāng)下的世界經(jīng)濟(jì)與政治格局,各國央行需要更多地對通脹保持高度警惕,而不僅是重點關(guān)注通縮風(fēng)險,《通脹的教訓(xùn)》的作者所總結(jié)的歷史教訓(xùn)和經(jīng)驗建議,無疑將大有裨益。
張立洲 《重塑經(jīng)濟(jì)增長》作者

 京公網(wǎng)安備 11010802028547號
京公網(wǎng)安備 11010802028547號